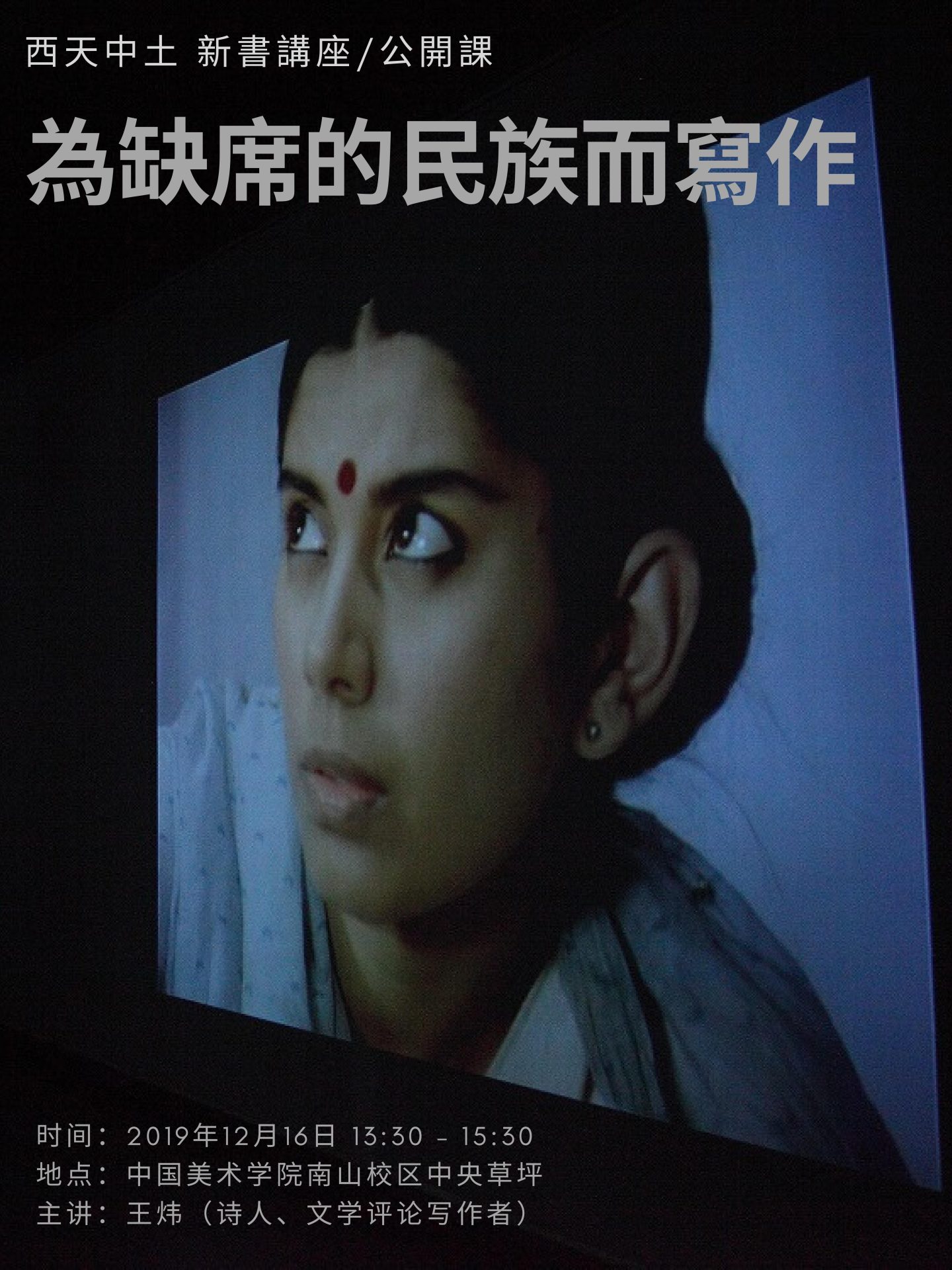2010
本文为“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的发言稿
或许是因为过去十年主编国际学刊《亚际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与亚洲各地(特别是印度)的批判知识圈产生了工作关系,所以张颂仁与高世名两位先生会找我一起组织2010年10月至12月于上海举办的“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的系列活动,由于理念相通,当然就义不容辞地参与了规划工作。他们分派给我的任务之一是替来访的印度学者的读本写序,给了我这个机会说清楚投入这次印中对话的思想背景。
十几年前推动建立《亚际文化研究》学刊的动力,是在有限能力的范围内去改变既有的知识状况,在学术生产的层面上推动亚洲各地的互动与整合。那个时候我们来自亚洲各地十几个地区的二十余位编辑委员对客观情势进行分析所产生的共识是:总的来说,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亚洲各地的知识圈都是把眼睛往欧美看,一个世纪下来,所有事物的基本参照体系都是欧美经验为主。百年之中,这个逐步建立起来的、极其稳固的知识结构,造成了学术思想上巨大的问题,不仅分析视野窄化,把欧美之外该参照的多元历史经验割除,更糟糕的是,欧美的知识方式几乎变成了唯一的典范。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套知识根本无法有效地理解、把握与解释我们自身的生存环境。如何透过亚洲不同次区域之间知识圈的互动,能够彼此看到,进而能使得各地的历史经验成为彼此的参照点,多元转化既有的参照坐标,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更具解释力的知识方式。就是凭借着这个认识论的共识,我们一起走了十年。
回头来看,这条路没有白走。虽然基本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上述的知识结构正在被快速地松动当中。过去十年世界情势的变化,正在确立世界是在走向多元并存的时代:拉美地区政权左转、东盟和东北亚“10+3”的形成、中国与印度的崛起、非洲经济持续成长、奥巴马政权取代布什政权、欧盟成员的继续增加等等。相较于1980年代末期,东欧、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倒台、美国强权一枝独秀主宰世界的“全球化”感觉结构,过去十年走向多元政治经济区域的变化,仿佛意味着一元世界的结束。在思想上,原来已经确定、凝固的知识体系及其所深信不疑的价值观,正在快速崩解当中,以欧美历史经验为基础形成的信心十足的解释框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处于变动的时代,放慢脚步、重新找回世界各地根植于现代历史经验的思想资源,于是成为开创新的知识状况难以跳过的路径。十年很短,《亚际文化研究》还没做出值得彰显的知识方式,但是至少我们已经上路了,尝试着走“亚洲作为方法”的知识路线。
在亚洲,乃至于其他的第三世界地区,既有主流的知识结构之所以会长期以“欧美作为方法”,还是得归咎于世界史的走向。在以欧美为中心向外旋转的力道下,中国也好,印度也罢,都是以“超/赶”(超英赶美)的基本姿势,学习欧美的事物(当然包括它的价值观),学术思想、知识生产于是被定位成国家民族现代化工程中的主要环节。姑且不要追究“超/赶”的知识方式中暗藏的陷阱,它是否混淆了规范性的目的与客观的历史解释力,至少可以开始问的问题是,一个多世纪下来,现代化的工程到底把原有的这些所谓后发国家变成了什么长相?民主也好,科学也罢,在学习后的搅拌中,实践出了什么新的模样?换句话说,是不是该停下脚步互相交换一些“超/赶”的经验,在欧美之外的地区之间,互相照照镜子,发现自己从过去变到现在的长相的路径?看清楚了,解释到位了,才能继续走下去,甚至进而发现“超/赶”的知识路线已经走到尽头,该是调整方向的时候了。
如果说知识的目的不是挑空了、为了知识而知识(首先预设了大写真理超越于历史的存在,用来笼罩整个世界),而是为了在世界史的范围内,从多元历史经验的视角,解释各地面对的不同的问题与处境,在相互参照、比较之中,慢慢提炼出具有世界史意义的知识命题,那么,可以说当前所有声称具有普遍主义性质的理论命题,都不成熟。以欧美经验为参照体系的理论,能够充分解释欧美自身历史就不错了,哪里能够解释其他地区的历史状况;反过来说,对于欧美以外地区的解释必须奠基在其自身历史发展的经验、轨迹当中,不能够简化地、错误地以欧美经验来丈量、解释自身。我想这正是应邀来访的著名的平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称之为“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的思想方案,或是2010年7月刚刚过世的沟口雄三教授之所以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思想精神之所在。
如果说欧美的历史经验只是一种参照的可能性,特别是它的发展经验与后发地区差距更大,那么在知识转化过程中需要被重新调整的——来访的印度女性主义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提出的策略——就是必须在欧美之外的地区开展出“替代性的参照框架”(alternative frame of reference),也就是把原来以欧美为参照,多元展开,以亚洲内部、第三世界之间为相互参照,经由参照点的移转,从差异中发展出对自身历史环境更为贴近的解释。这里思想方案的前提是:关起门来,以本土主义的自闭方式所产生的国粹主义,无法看清楚已经卷入现代的自我,只能沉溺在光辉的过去让自己继续感觉良好而已;打开门来,只以欧美为超赶的参照方式,已然失效,必须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本土主义(nativism)与欧美中心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两者之外,寻求新的参照体系。
我认为是在上述开启新的知识方式的问题意识下,“作为方法的印度”将会对中国学术思想界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中印之间能够产生对话的前提在于抛弃过去“超/赶”的认识论与知识方式,不能再以落后/进步、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等这些表象来进行比较。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得先摆脱、搁置规范性的比较,从分析上入手,看清差异,再开始提出内在于历史的解释。
印、中都是世界级的大国,农民占了人口最大的比例。资料显示印度目前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人口国,将在2026年达到十五亿,超过中国成为最大人口国;据估计,2015年印度经济的发展速度将超过中国。换句话说,抛开其他历史、文化的异同,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来说,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中,和中国最具可比性的就是印度,很难找到其他的地方。
但是,这两个国家也有巨大的差异。印度是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至今没有统一的语言,国会开会是要经过翻译的,所以很多印度的重要知识分子,如来访的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从来就不认为印度是欧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体。在被大英帝国征服以前,印度地区没有统合的政体,所以1947年从殖民地的身分独立以后也很难编织出数千年统一的民族历史,而必须更为多元复杂地理解它的过去。因为多民族的过去,在部分的人口中留下了所谓的种姓制度(caste system),到今天这个社会组织的原则还在运作,政治体制必须要去处理,无法简单地消灭它,而是要创造机制让底层的人口参与在政治过程当中。由于多语言的社会生存,文化差异与政治运作交叉重叠,不仅形成许多所谓区域性政党,连一些地方性政治人物(如省长),都是由特定语言产生的电影工业中制造出来的明星,以区域性的高知名度,经过普选选出。在此意义上,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运作根植于地方,全国性的政党都必须想办法跟区域性政治力量结合,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
对我个人而言,过去十几年进出印度,每次交流都有问不完的问题,因为南亚经验与东亚实在不同,摆在一起后者的情况变得相对单纯,各个国家、地区语言统一,民族国家面貌表面清晰,又不是多元政党,等等。这些有趣的差异,原来该是可以好好研究的,但是我大部分的中国朋友,大陆、香港、台湾都一样,把这些差异在已经习惯使用的“超/赶”的思路逻辑下,做了球赛式的比较:印度太长时间是殖民地,所以中国比较好(但是,别说台湾、香港地区曾经是殖民地,毛主席曾经说中国是半殖民地,连殖民地都还不是);印度政治制度是殖民体制的遗留,所以中国比较好,是经过孙中山、毛泽东革命建立起来的(反映的是再次贬低殖民地经验,把战后第三世界主义的世界观丢了);印度有种姓制度,所以中国比较好,封建制度已经消除(但是并不去追问印度过去的因子如何与当代社会接轨,反过来看看自己的社会中是如何与过去衔接,这个社会真是不再封建了吗);印度是多党的问题,谈的比较少,台湾的人会暂时忘掉欧洲的多党制,把美国两党制搬出来,说只有两党才进步(但是没法儿去问历史问题,印度的多党,乃至于区域政党是为何形成);还有些人说,印度到今天牛还在大城市马路上跑来跑去,哪有中国来得进步,不可能以印度为参照。总之,如果还是要用简单的“超/赶”逻辑,以欧美树立起来的简单的现代化指标来评比,那就只有等到印度经济超过中国,国力强大的时候,才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现在就继续向天上看吧!
其实,交流必然是双向的,其中会有许多难以避免的错位与误解,举例来说,印度知识界的许多朋友对中国感兴趣,并不是由于它的经济崛起,而是:中国“二战”后的社会主义阶段与今天经济发展的关系,长远形成的农民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以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为代表的平民研究关切的核心议题],社会主义体制与女性解放的问题至今产生了哪些变化,中国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中国广大的知识界对于世界的未来有什么不同于欧美的看法,知识界如何在自身的历史实践中提炼出对世界史的解释,等等。总之,以印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有基本的尊重,对中国知识界有一定的期待,都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与中国是否现代或是进步没有关联,但是,上述这些问题似乎并不是中国知识界感兴趣,或是准备好可以充分对话的(更让人难过的是,当第三世界地区期待与中国产生对话时,常常发现中国许多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根本不感兴趣,眼里只有欧美跟自己,还有人跟你说,别搞政治正确了,亚洲根本不存在,第三世界有什么值得对话的)。
我希望已经说清楚了“作为方法的印度”的前提,认识印度是为了去重新认识中国自身与世界,但是也知道当前的知识状况还是处于难以撼动的“超/赶”方式当中,欧美的价值观深入学术思想界,就连身处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陆知识界都很快在赶过港台地区战后“脱亚入欧/美”的知识状况,拥抱欧美知识体系的速度之快,远远超过经济发展,令人惊吓,所以对于这次试图开启的印中对话,并不抱持很大的希望,只是期待那些想找到其他道路的朋友,能够开始认识印度,为未来做准备吧。
这次活动邀请到的学者,除了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因为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很多著作都已经译成中文,其他几位,无论是否生活在印度,他们的知识构成都根植于印度社会与历史,在国际学术界都是非常有分量的学者,年龄上也横跨了三代,从1937年出生、1980年代就已在国际上赫赫有名的老将阿希斯·南迪,到在印度与国际思想界备受尊重、刚刚退休的帕沙·查特吉,以及九十年代初以后结构主义翻译理论成名的、壮年一代的文化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读本的翻译工程不小,为的是让中文世界的读者在与他们会面之前或是之后,能够对他们背后的印度社会、历史与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的机会。根据我的理解,这几位重要的思想者大都不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与想法,我们期待他们的来访,可以让中国的知识界能开始对印度也有相对应的深度认识,成为我们自我转化的契机。
本文为“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的发言稿
或许是因为过去十年主编国际学刊《亚际文化研究》(Inter-Asia Cultural Studies: Movements)与亚洲各地(特别是印度)的批判知识圈产生了工作关系,所以张颂仁与高世名两位先生会找我一起组织2010年10月至12月于上海举办的“从西天到中土:印中社会思想对话”的系列活动,由于理念相通,当然就义不容辞地参与了规划工作。他们分派给我的任务之一是替来访的印度学者的读本写序,给了我这个机会说清楚投入这次印中对话的思想背景。
十几年前推动建立《亚际文化研究》学刊的动力,是在有限能力的范围内去改变既有的知识状况,在学术生产的层面上推动亚洲各地的互动与整合。那个时候我们来自亚洲各地十几个地区的二十余位编辑委员对客观情势进行分析所产生的共识是:总的来说,在整个20世纪的历史进程中,亚洲各地的知识圈都是把眼睛往欧美看,一个世纪下来,所有事物的基本参照体系都是欧美经验为主。百年之中,这个逐步建立起来的、极其稳固的知识结构,造成了学术思想上巨大的问题,不仅分析视野窄化,把欧美之外该参照的多元历史经验割除,更糟糕的是,欧美的知识方式几乎变成了唯一的典范。但是,历史已经证明,这套知识根本无法有效地理解、把握与解释我们自身的生存环境。如何透过亚洲不同次区域之间知识圈的互动,能够彼此看到,进而能使得各地的历史经验成为彼此的参照点,多元转化既有的参照坐标,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更具解释力的知识方式。就是凭借着这个认识论的共识,我们一起走了十年。
回头来看,这条路没有白走。虽然基本格局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上述的知识结构正在被快速地松动当中。过去十年世界情势的变化,正在确立世界是在走向多元并存的时代:拉美地区政权左转、东盟和东北亚“10+3”的形成、中国与印度的崛起、非洲经济持续成长、奥巴马政权取代布什政权、欧盟成员的继续增加等等。相较于1980年代末期,东欧、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倒台、美国强权一枝独秀主宰世界的“全球化”感觉结构,过去十年走向多元政治经济区域的变化,仿佛意味着一元世界的结束。在思想上,原来已经确定、凝固的知识体系及其所深信不疑的价值观,正在快速崩解当中,以欧美历史经验为基础形成的信心十足的解释框架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处于变动的时代,放慢脚步、重新找回世界各地根植于现代历史经验的思想资源,于是成为开创新的知识状况难以跳过的路径。十年很短,《亚际文化研究》还没做出值得彰显的知识方式,但是至少我们已经上路了,尝试着走“亚洲作为方法”的知识路线。
在亚洲,乃至于其他的第三世界地区,既有主流的知识结构之所以会长期以“欧美作为方法”,还是得归咎于世界史的走向。在以欧美为中心向外旋转的力道下,中国也好,印度也罢,都是以“超/赶”(超英赶美)的基本姿势,学习欧美的事物(当然包括它的价值观),学术思想、知识生产于是被定位成国家民族现代化工程中的主要环节。姑且不要追究“超/赶”的知识方式中暗藏的陷阱,它是否混淆了规范性的目的与客观的历史解释力,至少可以开始问的问题是,一个多世纪下来,现代化的工程到底把原有的这些所谓后发国家变成了什么长相?民主也好,科学也罢,在学习后的搅拌中,实践出了什么新的模样?换句话说,是不是该停下脚步互相交换一些“超/赶”的经验,在欧美之外的地区之间,互相照照镜子,发现自己从过去变到现在的长相的路径?看清楚了,解释到位了,才能继续走下去,甚至进而发现“超/赶”的知识路线已经走到尽头,该是调整方向的时候了。
如果说知识的目的不是挑空了、为了知识而知识(首先预设了大写真理超越于历史的存在,用来笼罩整个世界),而是为了在世界史的范围内,从多元历史经验的视角,解释各地面对的不同的问题与处境,在相互参照、比较之中,慢慢提炼出具有世界史意义的知识命题,那么,可以说当前所有声称具有普遍主义性质的理论命题,都不成熟。以欧美经验为参照体系的理论,能够充分解释欧美自身历史就不错了,哪里能够解释其他地区的历史状况;反过来说,对于欧美以外地区的解释必须奠基在其自身历史发展的经验、轨迹当中,不能够简化地、错误地以欧美经验来丈量、解释自身。我想这正是应邀来访的著名的平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历史学家迪佩什·查卡拉巴提(Dipesh Chakrabarty)称之为“将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ing Europe)的思想方案,或是2010年7月刚刚过世的沟口雄三教授之所以提出“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的思想精神之所在。
如果说欧美的历史经验只是一种参照的可能性,特别是它的发展经验与后发地区差距更大,那么在知识转化过程中需要被重新调整的——来访的印度女性主义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Tejaswini Niranjana)提出的策略——就是必须在欧美之外的地区开展出“替代性的参照框架”(alternative frame of reference),也就是把原来以欧美为参照,多元展开,以亚洲内部、第三世界之间为相互参照,经由参照点的移转,从差异中发展出对自身历史环境更为贴近的解释。这里思想方案的前提是:关起门来,以本土主义的自闭方式所产生的国粹主义,无法看清楚已经卷入现代的自我,只能沉溺在光辉的过去让自己继续感觉良好而已;打开门来,只以欧美为超赶的参照方式,已然失效,必须在民族国家内部的本土主义(nativism)与欧美中心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两者之外,寻求新的参照体系。
我认为是在上述开启新的知识方式的问题意识下,“作为方法的印度”将会对中国学术思想界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中印之间能够产生对话的前提在于抛弃过去“超/赶”的认识论与知识方式,不能再以落后/进步、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速度等这些表象来进行比较。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得先摆脱、搁置规范性的比较,从分析上入手,看清差异,再开始提出内在于历史的解释。
印、中都是世界级的大国,农民占了人口最大的比例。资料显示印度目前是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人口国,将在2026年达到十五亿,超过中国成为最大人口国;据估计,2015年印度经济的发展速度将超过中国。换句话说,抛开其他历史、文化的异同,在社会科学的意义上来说,在世界上的所有国家中,和中国最具可比性的就是印度,很难找到其他的地方。
但是,这两个国家也有巨大的差异。印度是多语言、多文化的国家,至今没有统一的语言,国会开会是要经过翻译的,所以很多印度的重要知识分子,如来访的阿希斯·南迪(Ashis Nandy),从来就不认为印度是欧洲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文明体。在被大英帝国征服以前,印度地区没有统合的政体,所以1947年从殖民地的身分独立以后也很难编织出数千年统一的民族历史,而必须更为多元复杂地理解它的过去。因为多民族的过去,在部分的人口中留下了所谓的种姓制度(caste system),到今天这个社会组织的原则还在运作,政治体制必须要去处理,无法简单地消灭它,而是要创造机制让底层的人口参与在政治过程当中。由于多语言的社会生存,文化差异与政治运作交叉重叠,不仅形成许多所谓区域性政党,连一些地方性政治人物(如省长),都是由特定语言产生的电影工业中制造出来的明星,以区域性的高知名度,经过普选选出。在此意义上,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民主运作根植于地方,全国性的政党都必须想办法跟区域性政治力量结合,才能进行有效的统治。
对我个人而言,过去十几年进出印度,每次交流都有问不完的问题,因为南亚经验与东亚实在不同,摆在一起后者的情况变得相对单纯,各个国家、地区语言统一,民族国家面貌表面清晰,又不是多元政党,等等。这些有趣的差异,原来该是可以好好研究的,但是我大部分的中国朋友,大陆、香港、台湾都一样,把这些差异在已经习惯使用的“超/赶”的思路逻辑下,做了球赛式的比较:印度太长时间是殖民地,所以中国比较好(但是,别说台湾、香港地区曾经是殖民地,毛主席曾经说中国是半殖民地,连殖民地都还不是);印度政治制度是殖民体制的遗留,所以中国比较好,是经过孙中山、毛泽东革命建立起来的(反映的是再次贬低殖民地经验,把战后第三世界主义的世界观丢了);印度有种姓制度,所以中国比较好,封建制度已经消除(但是并不去追问印度过去的因子如何与当代社会接轨,反过来看看自己的社会中是如何与过去衔接,这个社会真是不再封建了吗);印度是多党的问题,谈的比较少,台湾的人会暂时忘掉欧洲的多党制,把美国两党制搬出来,说只有两党才进步(但是没法儿去问历史问题,印度的多党,乃至于区域政党是为何形成);还有些人说,印度到今天牛还在大城市马路上跑来跑去,哪有中国来得进步,不可能以印度为参照。总之,如果还是要用简单的“超/赶”逻辑,以欧美树立起来的简单的现代化指标来评比,那就只有等到印度经济超过中国,国力强大的时候,才会进入中国人的视野,现在就继续向天上看吧!
其实,交流必然是双向的,其中会有许多难以避免的错位与误解,举例来说,印度知识界的许多朋友对中国感兴趣,并不是由于它的经济崛起,而是:中国“二战”后的社会主义阶段与今天经济发展的关系,长远形成的农民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这是以帕沙·查特吉(Partha Chatterjee)为代表的平民研究关切的核心议题],社会主义体制与女性解放的问题至今产生了哪些变化,中国如何看待经济发展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的关系,中国广大的知识界对于世界的未来有什么不同于欧美的看法,知识界如何在自身的历史实践中提炼出对世界史的解释,等等。总之,以印度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对于中国有基本的尊重,对中国知识界有一定的期待,都与中国社会主义的政治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与中国是否现代或是进步没有关联,但是,上述这些问题似乎并不是中国知识界感兴趣,或是准备好可以充分对话的(更让人难过的是,当第三世界地区期待与中国产生对话时,常常发现中国许多的知识分子对他们根本不感兴趣,眼里只有欧美跟自己,还有人跟你说,别搞政治正确了,亚洲根本不存在,第三世界有什么值得对话的)。
我希望已经说清楚了“作为方法的印度”的前提,认识印度是为了去重新认识中国自身与世界,但是也知道当前的知识状况还是处于难以撼动的“超/赶”方式当中,欧美的价值观深入学术思想界,就连身处社会主义制度的大陆知识界都很快在赶过港台地区战后“脱亚入欧/美”的知识状况,拥抱欧美知识体系的速度之快,远远超过经济发展,令人惊吓,所以对于这次试图开启的印中对话,并不抱持很大的希望,只是期待那些想找到其他道路的朋友,能够开始认识印度,为未来做准备吧。
这次活动邀请到的学者,除了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因为是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很多著作都已经译成中文,其他几位,无论是否生活在印度,他们的知识构成都根植于印度社会与历史,在国际学术界都是非常有分量的学者,年龄上也横跨了三代,从1937年出生、1980年代就已在国际上赫赫有名的老将阿希斯·南迪,到在印度与国际思想界备受尊重、刚刚退休的帕沙·查特吉,以及九十年代初以后结构主义翻译理论成名的、壮年一代的文化理论家特贾斯维莉·尼南贾纳。读本的翻译工程不小,为的是让中文世界的读者在与他们会面之前或是之后,能够对他们背后的印度社会、历史与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的机会。根据我的理解,这几位重要的思想者大都不是第一次来到中国大陆,对中国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与想法,我们期待他们的来访,可以让中国的知识界能开始对印度也有相对应的深度认识,成为我们自我转化的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