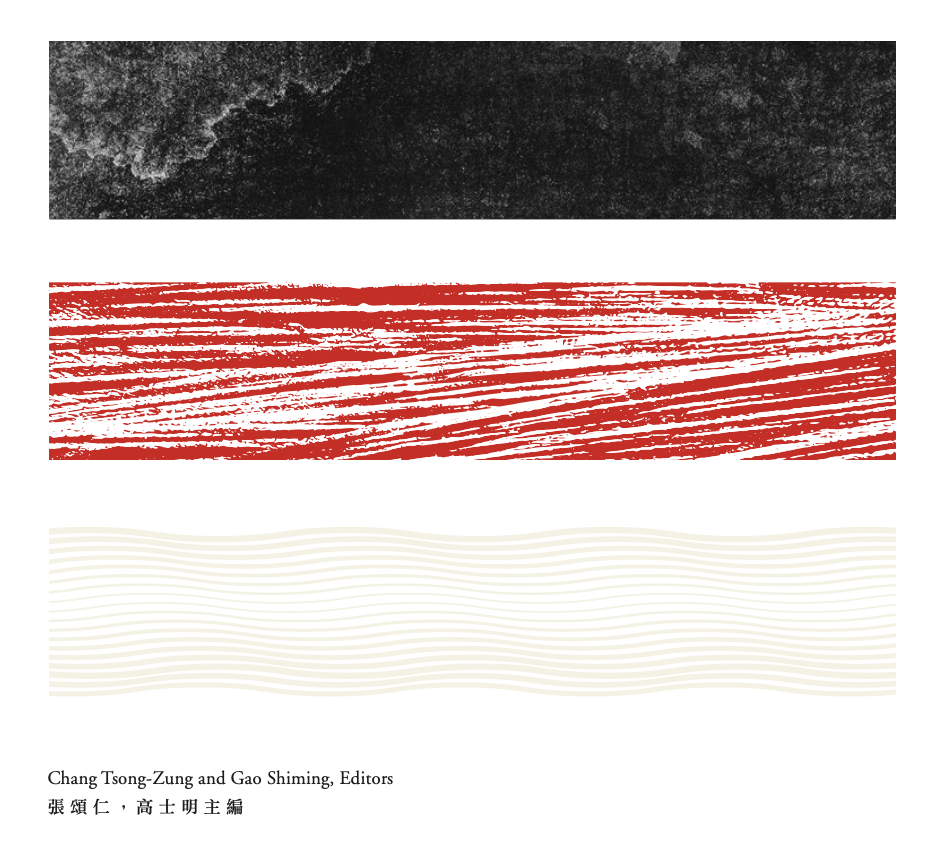2014-2015
本文为《人间思想02 三个艺术世界》导言,高世名、贺照田主编,人间出版社,2015年。
一
2008年春天,我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下这样一句话——我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是割裂的。这些年来,这句话时时浮上心头。的确,在研讨会上书空咄咄议论社会政治的我,与在昆仑、太行面前神为之夺的我判若两人,我之于“人间思想”的热情,较之面对山川造化的沉迷迥然有异。再说,何止我的自然观和历史观是割裂的,即使在艺术领域,我跟黄永砅、吴山专、邱志杰、汪建伟们讨论的艺术,与在山水画家的聚会中所谈论的,也似乎是全然不相干。于是,我的艺术观也是割裂的。
近几年与各个艺术圈子的朋友相知日深,这种割裂渐成自然。其实,在所谓“现代性”的百年流转中讨论“中国艺术”,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无限复杂的集合:从康有为的书法到黄宾虹的山水,从新兴木刻到“文革”宣传画,再到政治波普,从六七十年代的实验水墨到近来为市场追捧的“新水墨”,从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图,到张晓刚、曾梵志的油画,到黄永砅的装置和陈界仁的影像……林林总总,构成了一个艺术史的乱世。
这个乱世,或多或少地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
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自外于历史的生产过程。从我有限的艺术经历看,在这充满断裂的艺术史的乱世中,隐约浮现出三个艺术世界的投影:当代艺术的全球化世界(被认为是唯一的国际艺术平台)、文人的艺术世界(被建构为“传统”的往日云烟),以及社会主义文艺的世界(被告知已然终结)。这三个艺术世界并非如线性历史般接踵而至,而是在事件之流中交相激荡,彼此消长,在艺术史、社会史的斗争和运动中错综而为“当代”的汪洋。于是,我们惟有在文人世界、社会主义状态以及全球化体系的共时并存中,追索“艺术”的价值与意涵;在多种历史潜流的交响中,聆听来自不同艺术世界的消息;在当代中国的复杂境遇中,梳理这三个世界的现实性,探询其彼此交错的动力机制,发掘其历史潜能与势能。
2013年夏天,我从老友兼同事张颂仁先生数以千计的汉雅轩收藏中,选取了一百件以“艺术”为名的事物,聚集而为“汉雅一百:偏好”;并邀请中国美术学院当代艺术与社会思想研究所的青年研究员们,以这一百件事物作为策展素材,通过这些语境不同、线索各异的艺术“作品”之集合,梳理20世纪中国艺术的复杂历程,探讨“中国当代”的历史性结构。
2014年1月,“汉雅一百:偏好——中国现代艺术史中的三个艺术世界”专题展览在香港艺术中心与汉雅轩空间展出,我与张颂仁邀请了陈光兴、王晓明、陈清侨、北岛、贺照田等朋友,以及来自欧美各地的二十多位艺术界同人齐聚香港艺术中心,从艺术的角度,共同分享对于“中国当代”及其历史建构的理解。这次讨论提出三个议题:“三个艺术世界”、“分断与离散”以及“三个三十年”。
二
三十年来,中国两岸四地共同经历了国际风云的奇诡变幻——革命的退潮、冷战的终结、去殖民的抗争、全球资本主义的展开……三十年来,当代艺术在中国社会的种种变革与反复中发生、发展,从1980年代初的死水微澜到八五后的波澜壮阔,直至今日的蔚为大观,许多东西已然改变。
一方面,中国当代艺术在国际舞台与资本市场上取得了巨大成功;然而另一方面,这种成功归根结底,却是作为“另类现代性”、作为当代艺术地方版本的成功。对全球艺术展示装置的运作模式下,20世纪中国历史的这“三个艺术世界”若分而论之,各自会发展出所谓“中国性”、“中国牌”的某种景观。这些景观所导向的,是身份政治的成功,“中国牌”的成功,归根结底是全球资本的文化消费的成功。今天,我们再不甘于庆祝这种文化消费的成功,不再满足于在全球化的大厦中以“他者”之名争夺空间和地位,我们想要生产出新的空间,营造出一个不同的意义生产系统,一个文化创造、主体更新的历史性现场——那是三个艺术世界彼此沟通、相互策动的“中国当代”的现场。然而,对于这个历史现场,我们尚缺乏足够深刻的认识,甚至,我们还缺乏起码的分析话语和认知框架。
阿姆斯特丹大学的约翰·哈特勒(Johan Hartle)教授与张颂仁先生的论文聚焦“三个艺术世界”,以当代中国平行存在的三个艺术系统,批判性地回应了阿瑟·丹托(Arthur Danto)的“艺术世界”论述以及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的“全球艺术史”概念;在文人世界、社会主义状态以及全球化平台共时存在的当代中国现状中,探讨“中国艺术”对世界的贡献和可能走向。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翰·瑞哲曼(John Rajchman)对哈特勒与张颂仁所勾画的“三个平行艺术世界”图表,以及其所描绘的“制度的或社会学的诠释”提出了尖锐的质疑。在瑞哲曼看来,三个平行世界的制度化假说中,“没有任何提供目前创新或再思的空间……”在这幅制度图像中,“过去三十年的历史似乎已经关闭了”。他指出,在中国当代,“我们发现的远远不是‘非共时’或‘平行’时期的状态,而是复兴的‘无时’(a-chronic)时刻:意即不适合任何时期,有许多来源,朝向未知的未来……”因此我们应该思考——对中国历史上那些“场域”或者“制度框架”无法涵盖的狂热试验的初始时刻,“我们如何加以复兴、反思、重新创造,并在目前现况中重新捕捉其能量,不仅在中国境内,而是到整个世界?”比较起来,哈佛大学汪悦进教授的论文显得更为温和。他从中国艺术史不同时期的三件作品出发,意在揭示:“每件作品各自以一个意识形态世界为起点,但显然不完全沿意识形态的轨迹发展。它们既根植于特定时空,又与他界不断融合,不断暗示固定视野外的种种可能世界。”所以,“以三个世界发端,只是权借舟筏,以达视野模糊的彼岸。一旦开悟,舟筏可弃”。
作为策展团队的代表,中国美术学院的刘畑博士的论文中同样做了回应:“三个艺术世界”不是策展的“理论路径”,而是“理论对象”。三个“艺术世界”是三种不同的“生产方式”、三种历史过程导致的结果,策展的工作,恰恰是从这个理论框架所不包含的部分开始的。从这种意识出发,刘畑以“对无名的策展”为题,阐述了这群青年策展人从一百件“艺术物”中所收获的思想、感觉与信息,对家与国、分类与集合、历史与无名之学、民与众等观念进行了深度辨析。同济大学陆兴华教授则以作为收藏家的张颂仁为个例,探讨了收藏的激进意涵——对过去的保全、对历史的拯救以及对未来的开启。于是,“艺术地去保存”就意味着收藏家与革命家这两种角色的相辅相成;而“最高等级的收藏,是艺术,是保存,是要比我们时代的美术馆更可靠地使我们时代的收藏成为艺术,并利用这种艺术的自我保存,来保存我们的所保存,使之流传、挺持、残存、挥之不去……”对陆兴华来说,“汉雅一百:偏好”这个艺术物的集合保全了中国20世纪历史运动之外的许多风景,这一百幅作品构造出的,是那个世纪的运动、情感、革命、记忆、纪念碑之外的更远处的“造型的风景”。
时至今日,中国当代的艺术版图内部,依然充满了隔膜与分断——书画界与“当代艺术圈”老死不相往来,美协画家、画院画家与“当代艺术家”们莫不相知、相忘于江湖……即便如此,与被国际大展、博物馆和艺术市场构造出的“中国当代艺术”相比,当代中国的艺术生态依旧远为多元也远为复杂。此多元和复杂性不同于已经变得日益僵化而空洞的后殖民式的“杂糅”,也与欧美各国已经逐渐变为治理术的“多元文化主义”判然有别,中国艺术的多元依旧保持着内在的现实性与张力。因而“汉雅一百:偏好”所要做的,也就不是把这一百件艺术物分类安置于不同世界,而是要以变动不居的集合来呈现出三个世界之间的折射、穿越、交叠与混响。
三
历史没有终点线,我们都“在当代之中”。“在当代之中”,需要我们从历史的汪洋中打捞起所有的意义碎片,从彼此穿越、激荡的三个艺术世界中,打捞起那些在今天依然起作用的情感与智识,构建起一种扎根历史脉络、面向当下现实、具有主体意识的“中国当代”的文化视野。为此,我们必须打破中国“当代艺术”的通行历史论断,尝试着从20世纪的百年语境中,对中国现当代艺术史的叙述模式进行长时段的反思。
在中国大陆,对20世纪历史的叙述,往往被轻易地纳入三个三十年的论述框架之中——从1919到1949之间是“新文化三十年”、1949至“文革”结束是“新中国三十年”,“文革”之后至新世纪则被称做“新时期三十年”。对于这个漫长的世纪,现行的艺术史、文学史研究大多依据这三个时段分而治之,甚至学术界也依照这三个时段分为三个系统。如今,三个三十年同时叠加在当下的历史境遇之中,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三个三十年真正地贯通、聚合而为我们的“当代”视野?
回应“三个三十年”的议题,王晓明的发言阐述了现代百年中国的主流思想从“革命”到“反革命”的转向,以及这一思想转向所引起的社会意识的变迁,还有与之相关的文化生产机制的转换。他认为中国前卫艺术的历史不只是狭义的纵向的关系,更有多面的横向的关系,“前卫艺术是在这样的纵横交错的立体关系中形成”,他由此追问:“在百年来的中国的范围内,我们如何判定一种艺术或文艺是前卫的?是不是可以说,百年来相继登场的各种主流思想,以及站在它们背后的那些各不相同的支配性的文化生产机制,构成了一个至少与文艺的主流历史传统同样重要的参考坐标?”与王晓明的宏观勾勒相比照,贺照田的长文则从“汉雅一百:偏好”的展览中捻出“前卫”艺术家方力钧作为个案,抽丝剥茧地整理出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人的现实感觉、生命经验、社会意识与知识型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探讨了新时期文艺所未曾深挖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遭际与身心困扰。他从“文革”后三十年的精神史视野中,深刻剖析了中国前卫艺术机制的生成,以及它在理解和呈现当代中国人历史感觉、现实感觉方面的得失;并提醒我们,从当前的现实经验出发去重新追问——“中国前卫艺术为什么存在?如何存在?”
过去的一百年间,中国人所经历的不只是空间上的“区隔”和政体上的“分殊”,而且是历史的“分断”与命运的“离散”。这种“分断”与“离散”,折射到我们关于艺术的现代经验中,唤起一种复杂纠结、一言难尽的现实感。在20世纪中国文学艺术史的书写中,我们把“两岸三地”各自表述容易,但是贯通起来讲成同一个故事却异常困难。此事无关统独。真正值得思考的是,20世纪中国人经过了一次“大离散”,这“离散”的历史自殖民始,因政治“分断”而成。我们被分配到不同的意识形态阵营之中,被遣送到不同的政治体制之下,发展出迥然相异的历史意识和社会经验。这“大离散”,是冷战与殖民这两种历史力量交织塑造出的中国人的命运,也是20世纪众多非西方族裔的共同命运。今天,我们如何才能把这一历史命运回收到我们的思想和讨论中来?
来自巴基斯坦的策展人哈马德·纳萨尔(Hammad Nasar)以其策划的展览“控制线:作为生产性空间的分治”(Lines of Control: Partition as a Productive Space)中的六件作品为例,探讨了碎片化与弥散性、记忆与遗忘、共存与共享的切身命题,从而探讨当前处境中“分治”的生产性与现实效应:“分治”生育出民族,重写历史,重置记忆,定义边界并塑造巡视这些边界的手段和方法。中国台湾高雄师范大学跨域所的黄孙权教授剖析了他个人世界中的祖国、父国和母国,从个体生命史的角度阐述了分断与离散的历史结构下华人认同政治的复杂纠结,并质疑——“三个艺术世界是否如同海峡两岸暨香港此种牢固却过时的分断概念,再次凝固历史而非解放历史?”出生于中国香港的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程美宝的发言,一开始即提出“观念与历史”的辩证:分断与离散是概念,却包涵着悲欢离合的历史;而冷战是事实,但或许也不过是概念。程美宝的发言针对所谓后冷战时期香港社会逐步形成的“冷战体制”,思考抽象概念在反复的传播中,是如何变成“铁一般的事实”。冷战在哪里结束?后冷战从哪里开始?这原本就无法从历史中找到切实的答案。20世纪冷战正酣之际,香港多次成为祖国变乱的避难所和桃花源,而1989年冷战“结束”之后,海峡两岸暨香港的情感分断才真正“开始”。然而,许多时候,身世的“离散”和文化意义上的“分断”或许并不重合。正如我们从日本冲绳和中国金门的日常生活中所观察到的——升斗小民的生活足以穿越所有的政治分断与意识形态;也正如黄孙权所指出的“分断自是成王败寇的政治学,人民与土地是无法分断的,历史连续,而政治分断”。其实,在“汉雅一百:偏好”的展览中,最打动人心的,正是不同世代画面上那些“人—民—群—众—我”的身影与面容。
在本专题的最后,我们还收录了两篇“自传性”文本作为附录。艺术家邱志杰的〈我为什么要画水墨〉从切身出发,历述了他与水墨之间的因缘牵引。书法和水墨之于他早已超出工具与媒介,而是穿越并连接“三个艺术世界”的性命兼修的武器。20世纪的中国艺术家大都是杂食者,而邱志杰本人正是其中典范,正如他自己所言,他是“一个时代的精神混乱,和一个民族的精神病史的病例。三十年不眠不休,欲壑难填,上天入地,正邪兼修,激烈地卷入历史和世界……”张颂仁的〈三十年物缘〉则从香港独特的历史视角出发,梳理了他的20世纪经验,以及此经验所产生的辩证与纠结、恐惧与困惑。“全盘的历史方案永远无法毫无遗漏地整合天下”,所以他身上所容纳的这“三个世界”之外,总还有“其他无法清楚辨识的因素和无名的动力”。“三个艺术世界”在他这里绝非观念,亦非场域或者制度,而是其真实身世的一部分,他对于此历史结构的反思因而带着切肤之痛,他对其“意底牢结”的告解也因而焕发出涤荡人心的力量。
四
脱开线性叙事的幻相,历史乃是一片汪洋,所谓“当代”只不过是海面。海面只是我们看上去的那层“表面”幻相,实则与大海同体无间。这一片汪洋,起伏不定,动荡纵横,在我们身体内外穿梭往复。它不但“无界”,而且“有情”。从这一片汪洋之中,我感知到历史的宏大进程。
历史进程一言难尽。在中国人复杂纠结的百年历程中,我们感知到“中国当代”的历史性构造。透过当代起伏不定的海面,我们回望、经验并且辨识着现代百年的记忆与过往——华夷之辨、中西之争、帝国的阴影、人民的形象、家国的幻灭、革命的烈火、改革的一波三折、市场的激流涌动……这进程裹挟着无数人的身世与命运,演绎出百余年来中国人的抗争和寻觅、离合与悲欢。
身处这复杂纠结、泥沙俱下的宏大进程之中,我们何以自处?艺术如何作为?
从“与后殖民说再见”(2008)到“排演”(2010),再到“八五·85”和“进程”(2013),在数度策展演习之中,我逐渐意识到:所谓中国当代,是革命/后革命、殖民/后殖民、冷战/后冷战……这些历史力量胶着混战后狼藉的战场,而“当代艺术”,则是这反复拉锯的历史剧场上文化斗争的因果建构。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在帝国与民族国家的双重结构中被重新切分,在殖民史和冷战史的交织纠缠中分断与离散,在全球化的生产-消费网络中被不断地分配与整合。就中国大陆而言,在革命、回归、殖民、冷战等多重历史动力的交互作用下,当代的艺术生态并未被完全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的网络之中,传统书画的风尚和收藏系统依然健在,国家委托创作的运作机制一息尚存,这些系统与双年展、博览会的国际机制彼此渗透、影响。相较于欧美国家的艺术世界,“中国当代”显示出一种独特的复杂性与多义性。然而,另一方面,无论是风雅犹存的书画界,还是代表政治“主旋律”的美协、画院,或者是以挑战、反叛自诩的当代艺术界——20世纪遗留给“中国当代”的这三个艺术世界,此刻却都以各自的方式与资本勾结,与时尚合流。在这大陆艺术界浮华世事的背后,“兴、观、群、怨”、创造与批判、革命性与群众性、改变生活、改造社会……这些曾经对艺术性命攸关的意义,现在都已然丧失殆尽。在中国当代,艺术丢失了它的任务书,“当代艺术”已逐渐沦为当代社会的失业者。
在我写作这篇序言之际,台湾、香港的社会运动正如火如荼。与大陆同行们不同,台湾、香港的艺术家们带着各自的理论装备,或者深入田野,或者轰轰烈烈地卷入到社会运动之中。然而,这次社会运动的浪潮却令我不安。“占领立法院”、“占领中环”与几年前的“占领华尔街”表面上如此相近,在政治取向上却又如此不同。事实上,许多长期参与现实运动的艺术人与知识人,这一次都深感左右为难。在港台两地,现实政治中的右翼正颇为顺手地操持着左派话语,而知识左派在现实政治中的主张与右翼却越来越难以区分,这使得他们在现实斗争中日益失语或者失据。知识左翼在这一轮社会运动中被轻易地收编,又被无情地抛弃——香港发明了“左胶”、台湾抹黑了“左统”。在大陆,表面上的“政左经右”、“形左实右”,掩盖的是远为纠结的现实;尤其当我们从政府话语-知识话语-民众话语的多层面的动力机制中,在官方媒体-大众媒体-自媒体的多重映射关系中进行深入考察的时候,问题更显复杂。目前的问题是:没有对自媒体社会的政治/情感状况的系统分析,没有对生命政治背后的政治经济学状况的深入洞察,我们实难理清今日的社会意识和现实境遇,艺术家们的诸种政治参与,或许只是在拿着过往的问题意识和旧的思想工具作为道具进行角色搬演而不自知。
热切卷入社会运动的艺术家们需要自我追问的是——“运动之后”是什么?一切运动都在期待着某种革命式的反转或开端,无论这革命为的是更大的平等、更彻底的自由、更充分的民主,还是被习惯性地当作目标/依托却未必靠得住的普选。然而,当那个被历史神圣化的时刻迟迟不来,我们陶醉其中的“暴雨将至”逐渐风流云散,一切革命的期许终究会被日常生活腐蚀、击败。
运动之后是什么?在全球范围内,艺术与社会运动的合流、Artist as Activist(作为行动者的艺术家)的宣称已经流行了半个世纪。无论在大陆、台湾还是香港、澳门,无论是在北京还是纽约,在今天这个“大数据-全媒体-后网络”的时代,艺术的现实境遇已经悄然变化。社会参与、体制批判、政治艺术或美学政治……所有这些流行或者过时的话语已经不足以匹配我们此刻的现实感受。在景观资本主义的时代,生产关系对人之劳动价值的“剥削”,已经转化为生命政治对人之能动性的“剥夺”;我们的现实处境正如陈界仁所言,是“全球监禁,在地流放”。在这样的处境中,我深切地感到,1960年代文化政治氛围中开启的这段社会参与的艺术史已经走到了尽头。
或许,此刻正是世界艺术史的幕间状态。一幕已经结束,下一幕尚未开启。在这个幕间时刻,对承载着三个艺术世界的我们来说,迫切需要思考的是:如何从文人世界的情怀中提取出一种对世界的精微感受力?如何从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中发展出一种集体性的“公”的创造力?如何从今天新兴技术媒体的激进现实中,发展出一种充分介入日常世界的新艺术?如何从民众复杂的历史感和现实感中,提炼出一种深度参与社会进程的新艺术?
“运动之后”是疲惫与迷茫,“幕间时刻”空虚而困顿。而下一幕大戏、艺术的破局与开局,或许正在迷茫与困顿中酝酿展开。只要我们相信——每一次幕间时刻,都将是革命的前夜。在下一场革命开启之际,这尚未到来、即将到来的新艺术,将会是生产的艺术、行动的艺术、民众的艺术和解放的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