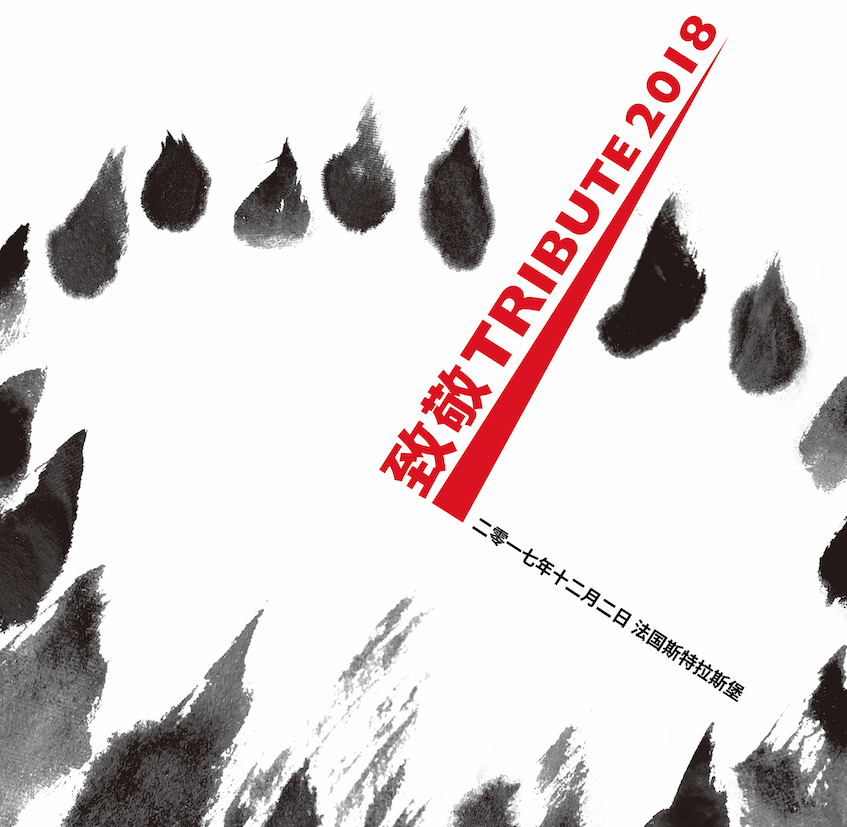2019
本文在2019年3月中国美术学院的演讲稿基础上写成,原载杭州《新美术》2020年12月号,此版本有增补。
区辨中西景观文化中的“山水”与landscape(或paysage)可以有多种角度,本文尝试从一个新角度,即对森林的态度加以区辨,并希望借此进一步从历史语境中理解和界定“山水”。
一、中西传统艺文中的森林
罗马时代的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23—79)在其百科全书式的巨著《自然史》中说:“树与森林应当是自然赋予人的最高恩赐。”[1] 中国古代的山水艺文,是以大自然景物为内容的。然而,在东晋“山水”作为新语词随士人游赏山水出现以后,林中之人的视野在以“山水”标示的绘画和文学中几乎难得一现。简单点说,作为大自然予人最高恩赐的森林只是山和水中的附属部分,而不能成为表现的主体,即如宋人郭熙所说,山“以草木为毛发”[2],林木如山水画中的人物、楼观,皆为山之附件:
山之人物,以标道路;山之楼观,以标胜概;山之林木映蔽,以分远近。[3]
韩拙论山水画中林木时,以下面的文字表达了类似看法:
其有林峦者,山岩石上有密木也;有林麓者,山脚下林木也;林迥者,远林烟暝也。……林木者,山之衣也。如人无衣装,无仪盛之貌。[4]
为验证上述两位论画者的看法,不妨重温古人画笔下凸显林木的作品:董源《潇湘图》隔水见山麓江渚有数簇疏林,文征明《仿米氏云山图》在云山下江湄上点缀丛林,王鉴《长松仙馆图》在山下溪谷乱石间画森森林木,是所谓“林麓”;巨然《秋山问道图》山岩上时见簇簇林木郁茂,沈周《庐山高图》画山岩悬淌瀑布,两侧散有林木,王原祁《浅绛山水》画山峦上下时见林木,是所谓“林峦”;江参《千里江山图》、王希孟《千里江山图》、赵孟頫《重江叠嶂图》、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等长卷,皆于远山遥水间点缀林木,是所谓“林迥”。在以上所有画幅中,林木真的不过是“山之衣”,水之垂绅而已。古代画家中,元四家之一王蒙或许最喜写林木,其《太白山图》《夏山高隐图》《林泉清集图》等作品竟让林木占据了近半画幅。然即便如此,由于画家乃自太虚而俯瞰,仍然不是林中人的视野,森林纵深究竟十分有限。
体现中国景观的又一文化类型园林或园亭,乃以水石和亭榭为主体,花木只是陪衬。自以花坛(parterre)为主的法国花园或以林木为主的英国花园传统看来,中国造园对植物的兴趣显然有所控制。[5] 故而,西方读者读《红楼梦》,会感到小说家出于将少女隐喻为花的动机,令大观园中的花木构成相比真实的中国园林做了夸张。以花园(garden)来指称借叠山理水造就的中国园亭,严格说来并不恰当。
那么,作为中国中古文学主要样式的诗歌又究竟如何?中古诗人书写山林不外乎几种可能的境况。首先是游览,此时平野之上恐多为田畴,游览不登山则难入深林。鲍照、谢朓诗作中可归在“游览”名目下的游山之作,在沿袭大谢诗风之时,约略地写到林木。如鲍照的《登庐山》有“耸树隐天经”[6],《登庐山望石门》有“韬树必千祀”[7],《从登香炉峰》有“青冥摇烟树”[8]。谢朓写到森林的只有《游山诗》中“傍眺郁篻簩,还望森柟楩”和《游敬亭山》中“交藤荒且蔓,樛枝耸且低”两联。[9] 江淹《游黄檗山》在观赏“金峰”“铜石”之余,见山中“残屼千代木,廧崒万古烟。禽鸣丹壁上,猿啸青崖间”[10]。孟浩然登临望楚山所写《登望楚山最高顶》竟未有一语涉林木。李白游览东岳所写《游泰山》六诗,只以偶或出现的“松声”“扪萝”“松风”令人隐约想到山上或有森林。李白登巫山最高峰题诗于壁,亦只以“积雪照空谷,悲风鸣森柯。……江寒早啼猿,松暝已吐月”[11] 数语暗示:他可能于攀登之中经过了森林。韩愈的《南山诗》,这首描绘山景的迭迭千言之作,写到林木仅有两处:“夏炎百木盛,荫郁增埋覆”[12] 是夏山之概貌;“杉篁咤蒲苏,杲耀攒介胄”[13] 是一瞥冰雪山林之景象。而此诗最后以五十一个“或”字展开的铺张,却全然是众山之形势。显然,森林从不是诗人游览的目的地,不过是为一览高处胜景而在攀登过程中掠目而过的景象而已。
其次,诗人可能会在行旅经过深山时接触森林而书写森林。江淹自越入闽路经的泉山,即四百多年后黄巢“刊山开道七百里,直趋建州”[14] 的仙霞岭,江淹有《渡泉峤出诸山之顶》记述这次入闽的艰难,诗中写道:
岑崟蔽日月,左右信艰哉。万壑共驰骛,百谷争往来。……崩壁迭枕卧,崭石屡盘回。伏波未能凿,楼船不敢开。百年积流水,千里生青苔。[15]
诗人写行旅艰险,关注的是以“岑崟”“万壑”“百谷”“崩壁”和“崭石”指称的山岩岭谷地貌,以及“流水”,竟未能有一言涉及遮蔽日月的森郁之林!
诗史上另一组入山行旅的名作是杜甫由秦州经同谷入蜀所写的二十四首诗。这一条入蜀的山中险路,其时应当经过为原始林莽覆盖的区域。诗人尽管以入化之笔绘写路途景色,但在阁路栈道随山形水势延伸之时,其游目始终首先关注着天-地框架下的山水,即便时或写到林木,也附着于此,如:
径摩穹苍蟠,石与厚地裂。修纤无垠竹,嵌空太始雪。[16]
冈峦相经亘,云水气参错。林迥硖角来,天窄壁面削。……仰看日车侧,俯恐坤轴弱。[17]
远岫争辅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仰干塞大明,俯入裂厚坤。再闻虎豹斗,屡局风水昏。高有废阁道,摧折如断辕。下有冬青树,石上走长根。西崖特秀发,焕若灵芝繁。润聚金碧气,清无沙土痕。[18]
栈云阑干峻,梯石结构牢。万壑欹疏林,积阴带奔涛。[19]
诗人经阁路栈道入蜀,尽管一路林木森郁,时而听到虎豹熊罴的咆号,但他并没有特别的机会,更没有特殊的兴趣,去进入深林一窥究竟。
古代旅行更多会借助舟船。近岸舟行之时,深林掠过帆樯,诗人可投骤然一瞥。何逊因而有“硣磟上争险,岞崿下相崩。百年积死树,千尺挂寒藤”[20]。杜甫大历三年春的出峡舟行之作更为精彩:
窄转深啼狖,虚随乱浴凫。石苔凌几杖,空翠扑肌肤。叠壁排霜剣,奔泉溅水珠。杳冥藤上下,浓澹树荣枯。……[21]
诗人是在扑面而来的林木作迅疾一瞥。当然诗人更可能是于中流眺望岸上森林,如江淹的“吴江泛丘墟,饶桂复多枫。水夕潮波黑,日暮精气红”[22],何逊的“山烟涵树色,江水映霞晖”[23],孟浩然的“桂楫中流望,京江两畔明。林开扬子驿,山出润州城”[24]……皆是。不用说,隔水远眺是更不可能深入到森林内部的了。
最后,诗人可能因隐居深山而书写森林。然而,倘非谢灵运所说的“甘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颓形”的森林苦行僧人,又非韦应物所咏的“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25] 那样的山中道士,结庐亦不在深林。陶渊明自谓“结庐在人境”[26],周边见“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27];王绩“家住箕山下,门枕颍川滨”,“朝朝访乡里,夜夜遣人酤”[28];孟浩然自谓其庐“左右林野旷,不闻朝市喧。钓竿垂北涧,樵唱入南轩”[29],旧传隐在汉水东岸鹿门山,其实在汉水西畔一片滩涂地上;[30] 王维嵩山隐居之所是“清川带长薄,车马去闲闲”[31],淇上之所是“屏居淇水上,东野旷无山。日隐桑柘外,河明闾井间”[32],居辋川别业则能见“渡头余落日,墟里上孤烟”[33]……既卜庐人境,故也只能在采樵时深入山林了。但这样的诗作寥寥无几,王维和孟浩然只各写过一首:
采樵入深山,山深树重叠。桥崩卧槎拥,路险垂藤接。日落伴将稀,山风拂萝衣。长歌负轻策,平野望烟归。[34]
檀栾映空曲,青翠漾涟漪。暗入商山路,樵人不可知。[35]
据以上讨论,不难推导出一结论:中古以后中国士人的主要生命活动已无关“深林”。即便宦游行旅也基本在水陆馆驿之间的驿路和阁道上进行,隐居也结庐于“人境”之中。结庐之处和行旅之途周边纵有森林,然如中古时代中土已几无森林神祇一样,士人也多无游赏森林之风气。中国士人对自然景观的主要兴趣,即为山/水所概括。
中国传统叙事文学中森林也少被述及。《三国演义》中刘备、陆逊的猇亭、彝陵之战,《水浒传》鲁智深大闹野猪林、景阳冈武松打虎这些情节皆发生在山林,但作家对此背景只是点到即止。《三国演义》为写陆逊因势用火攻而有“先主遂命各营,皆移于山林茂盛之地,近溪傍涧”;《水浒传》为写鲁智深从薛霸、董超水火棍下救林冲而有“早望见前面烟笼雾锁,一座猛恶林子,有名唤做野猪林”;又为写武松打虎而有“只听得乱树背后扑地一声响,跳出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来”。在这些森林出现的环境,作家从未有兴趣对森林景观作任何渲染。而且,森林在此皆为灾难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的地点,绝非“喜剧性转变的完成之所”。
然而,森林这个主题或题材,却在欧洲文化中有着全然不同的位置。倘佯于欧洲艺术博物馆即会发觉:欧洲近代绘画的风景主题,在文艺复兴之初从古典神话和宗教主题里辗转出现。古典神话题材中多涉风景自然的潘神、宁芙、赛特等都是森林中的自然神;基督教题材常用来表现风景的是伊甸园、圣母玛利亚逃亡埃及、魔鬼诱惑耶稣和林中修道的圣父,背景都是森林,即便《马太福音》叙写玛利亚携圣婴逃亡时其实并未提到森林。[36]
欧洲文学中的大自然同样离不开森林。传说中最早的希腊诗人安菲翁(Amphion)的歌唱就是献给林神(Satyrs)的,他的林神剧据说是希腊悲剧的渊源。[37] 罗马诗人奥维德(Publius Ovidius Naso)所撰《变形记》中,阿克泰翁是因在森林深处撞见了正在洗浴的森林女神狄安娜和一行宁芙们,而被变为了鹿;纳西修斯坠入自恋的那个清纯池塘也在密林深处;他笔下那位最美的宁芙为逃脱潘神追逐,化作一根芦苇之前先进入了森林。维吉尔(Virgil)的史诗《埃涅阿斯纪》(The Aeneid)中,“森林与狩猎、战斗、流放和死亡象征性地联系在了一起”[38],此书第九卷中,欧律阿鲁斯和尼苏斯被追赶而逃入森林,他们最终都死在森林里。但丁在《神曲》地狱篇中也走入一片幽暗森林,在此他遇到了维吉尔。14世纪佚名文本《戛文先生与格林骑士》(Sir Gawain and the Green Knight)中,阿瑟王麾下的戛文骑士为寻找格林骑士进入了猛兽出没的密林。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的史诗性作品《帕兹瓦尔》(Parzival)中,圣杯骑士帕兹瓦尔成长于密林。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仙后》(The Faerie Queene)中,红十字骑士为解救被巨龙囚禁的尤娜父母,和尤娜进入了迷踪之林;异教骑士赖斯将尤娜带入有土著居住的密林。桑德斯故而说:森林是“罗曼史人物的特有领土”,无边无际的森林成为“可以满足罗曼史故事的原因”。[39] 更不必说司各特(Walter Scott)《艾凡赫》(Ivanhoe)中罗宾汉的舍伍德森林,以及格林童话中七个矮人的森林。以弗莱的说法,绿色森林又是莎翁浪漫喜剧的典型场景,[40] 在《仲夏夜之梦》《皆大欢喜》《温莎的风流妇人》《冬天的故事》中一再出现,情节从一般人间世界经过绿色森林再回到人间,森林成为“喜剧性转变的完成之所”[41]。在抒情诗中,描绘大自然的里程碑式巨著——汤姆森(James Thomson)洋洋数千行的《四季》(The Seasons)中,诗人写到春日的森林宁静中,林木在簌簌颤动中生长;写到他踩着树叶的各种阴影漫步;写到森林在暖风中膨胀,各种自然的音符苏醒了,与溪流合成野性的交响乐;写到狮子在阴郁的林中出现,心灵变得柔顺;写到森林如何邀请他加入百鸟歌声和林木呼吸组成的爱之旋律;写到夏日清晨的密林,阳光穿不透枝叶的阴郁,溪水蜿蜒在暗绿的草丛里,又在橡树的粗根上流淌;写到晨光中野兔怯生生地跳跃,林中空地上野鹿在张望早来的旅人;写到刚失去配偶的斑鸠在林中哀鸣;写到在午间的炙热空气中野火如何吞噬成片的巨木,烧枯的树干下躺卧着烤焦了的成群的野牛。诗人也写到秋日自欹斜的森林里时不时吹洒的落叶之雨,如何旋转着被卷入山谷……这些都是诗人所经历或所设想的身在密林深处的体验,诗中展开的是林中之人的视野。
欧洲的花园也常常被森林环抱。如法国卢瓦尔河谷以香波堡为代表的几座著名王室城堡花园就坐落在王室狩猎森林之中。巴黎南郊枫丹白露宫的几个花园和代表法式园林开端的沃子爵堡(château de Vaux-L-Vicomte)花园皆为枫丹白露森林所环抱。凡尔赛宫的南部也是森林。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卡塞塔王宫花园是全欧最大的花园之一,中轴线长达数公里,其尽头石山虽然少有林木,但主花园一侧却是个被各种林木浓密覆盖的英国花园。哈布斯堡王朝的宫殿花园由于建在维也纳城市之中,但两侧也常以浓密的林木象征森林……所有这样的设计似乎在暗示:这是藏在林中的一方乐土,隐隐透显出《创世纪》中伊甸园的影子:“在园中神让每一种悦目的和果实能充饥的树木生长,生命之树和善恶知识之树也在其中。”[42] 而现存中国园林却没有被森林簇拥的例子。
当然,在做以上的比较和概括之时,不应忽略例外情况。中国山水诗的开山人物谢灵运,在中国诗人中恐为最多地写到了森林的一位,尽管森林的书写在其笔下附丽于山、水形势,远未取得山与水在话语中的凸显位置。谢灵运的《石门新营所住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登石门最高顶》和《石门岩上宿》诸诗还显示:他甚至有夜宿森林的经验。[43] 相对一般文人,特别是后来的文人,这颇不寻常。然如其《山居赋》所明言,这一切乃为践行释氏之教:
山野昭旷,聚落膻腥。故大慈之弘誓,拯群物之沦倾。岂寓地而空言,必有贷而善成。钦鹿野之华苑,羡灵鹫之名山。企坚固之贞林,希庵罗之芳言。[44]
同赋之中,谢灵运更直接透露:他经营石门住所、夜宿山林是受到两位“苦节之僧”昙隆和法流的感召:
苦节之僧,明发怀抱。事绍人徒,心通世表。是游是憩,倚石构草。寒暑有移,志业莫矫。观三世以其梦,抚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东山以冥期,实西方之潜兆。虽一日以千载,犹恨相遇之不早。谓昙隆、法流二法师也。二公辞恩爱,弃妻子,轻举入山,外缘都绝,鱼肉不入口,粪扫必在体,物见之绝叹,而法师处之夷然。诗人西发不胜造道者,其亦如此。往石门瀑布中路高栖之游,昔告离之始,期生东山,没存西方。相遇之欣,实以一日为千载,犹慨恨不早。[45]
这段赋文及后面的作者自注透露:其“往石门瀑布中路”的“高栖之游”是在效法二僧人“倚石构草”的苦行。“西发”和“石门瀑布中路”表明这就是其诗所涉之“石门新营所住”,地点在今嵊州崇仁镇马家田,该处至今仍可见“四面高山,回溪石濑,修竹茂林”[46] 的景观。谢氏笃信释氏,才会在《临终诗》中发出“恨我君子志,不获岩上眠”[47] 的慨叹。居住山林与佛教的关系,更可证之以同期佛教僧人居处山林的记载:
帛僧光或云昙光……少习禅业。晋永和初,游于江东,投剡之石城山。山民咸云:此中旧有猛兽之灾,及山神纵暴,人踪久绝。光了无惧色,雇人开剪,负杖而前。行入数里,忽大风雨,群虎号鸣。光于山南见一石室,仍止其中,安禅合掌,以为栖神之处。……光每入定,辄七日不起。处山五十三载,春秋一百一十岁。[48]
竺昙猷,或云法猷,敦煌人。少苦行,习禅定。后游江左,止剡之石城山,乞食坐禅。……后移始丰赤城山石室坐禅。有猛虎数十,蹲在猷前,猷诵经如故。一虎独睡,猷以如意扣虎头,问何不听经?俄而群虎皆去。有顷,壮蛇竞出,大十余围,循环往复,举头向猷,经半日复去。后一日神现形诣猷曰:“法师威德既重,来止此山,弟子则推室以相奉。”猷曰:“贫道寻山,愿得相值,何不共住?”神曰:“弟子无为不尔,但部属未洽法化,卒难制语。远人来往,或相侵触。人神道异,是以去尔。”猷曰:“本是何神?居之久近,欲移向何处去耶?”神曰:“弟子夏帝之子,居此山二千余年。寒石山是家舅所治,当往彼住。”寻还山阴庙。临别执手,赠猷香三奁,于是鸣鞞吹角,陵云而去。
赤城山山有孤岩独立,秀出干云。猷抟石作梯,升岩宴坐,接竹传水,以供常用,禅学造者十有余人。[49]
支昙兰,青州人。蔬食乐禅,诵经三十万言。晋太元中游剡,后憩始丰赤城山,见一林泉清旷而居之。经于数日,忽见一人长大数,呵兰令去。又见诸异形禽兽数以恐兰,见兰恬然自得,乃屈膝礼拜云:“珠欺王是家舅,今往韦卿山就之,推此山以相奉。”[50]
释法续,姓混,高昌人。德行清谨,蔬食修禅。后入蜀,于刘师冢间头陀山谷,虎凶不伤。[51]
释僧从,未详何人。禀性虚静,隐居始丰瀑布山。……不服五谷,唯饵枣栗。[52]
吾人须留意:以上五位僧人深居林莽,是延续天竺佛教部派以前的山林居住传统。五则事迹中,四则发生在浙江中部,与谢灵运隐居的始宁属同一地区。又有四则事迹中出现了山林的象征猛兽,其中仅虎就出现四次,此外还有“壮蛇”和“异形禽兽”。曾于石城山中“木食涧饮,浪志无生”[53] 东晋名僧支遁,也一再以诗吟咏在山林栖禅的僧人:
云岑竦太荒,落落英岊布。回壑伫兰泉,秀岭攒嘉树。蔚荟微游禽,峥嵘绝蹊路。中有冲希子,端坐摹太素。[54]
晞阳熙春圃,悠缅叹时往。感物思所托,萧条逸韵上。尚想天台峻,髣佛岩阶仰。泠风洒兰林,管濑奏清响。宵崖育灵蔼。神蔬含润长,丹沙映翠濑。芳芝曜五爽。苕苕重岫深,寥寥石室朗。中有寻化士。外身解世网。抱朴镇有心,挥玄拂无想。[55]
在士人游赏“山水”风气出现后,对“山林”的兴趣,皆出于佛教信徒栖处深山苦节和习禅的动机。对唐代王维的《辋川集》中的《鹿柴》《竹里馆》,诗僧寒山的《家住绿岩下》《夕阳赫西山》《可重是寒山》《山中何太冷》《寒山多幽奇》一类诗作亦应作如是观。
谢灵运《山居赋》在叙述了其石门山栖的缘由之后,曾讨论了道教仙学与山林的关系,谓求仙者纵然“未及佛教之高,然出于世表矣”,比之世俗之徒,毕竟是“松菌殇彭,邈然有间”[56],故而亦将其纳入缅绝世缨而甘松桂之苦的山居之士中。诗史中最能体现仙道之学与森林关联的人,恐怕是“怀抱道经,独坐空山”的江淹。其以屈宋笔墨描绘了一幅“深林”图画:
桐之叶兮蔽日,桂之枝兮刺天。百谷多兮泻乱波,杂涧饶兮鹜丛泉。……山峦岏兮水环合,水环合兮石重沓。林中电兮雨冥冥,江上风兮木飒飒。
绁余马于椒阿,漾余舟于沙衍。临星朏兮树闇,看日烁兮霞浅。浅霞兮驳云,一合兮一分。映壑兮为饰,缀涧兮成文。碧色兮婉转,丹秀兮芬蒀。深林寂以窈窕,上猿狖之所群。群猿兮聒山,大林兮蔽天。枫岫兮筠岭,兰畹兮芝田。[57]
仙道之学和屈宋之辞,又都指向了一个渊源——即闻一多所说的“古道教”或萨满巫术。[58]
容本人回到上文所征引的《高僧传》中竺昙猷和支昙兰颇具奇幻色彩的事迹。这两则故事中,赤城山神都将山林最终拱手奉予了僧人。一位山神且自称是“夏帝之子,居此山二千余年”。这个故事似乎在寓示:纵然释氏僧人入林修禅,去离俗世,然随着僧人到来,作为“夏帝之子”的华夏上古山林之神所拥有的“未洽法化”的野性大自然就也消失了。高僧遁入深林坐禅驯化了猛兽的故事,让吾人联想到欧洲中世纪手持十字架进入森林修行的基督教圣徒驯化野兽的事迹。这类成为了高僧或圣徒的佛教僧人的森林,已不再是真正的原始森林了。这让吾人好奇:中国古代典籍中是否还存留着对“夏帝之子”曾经居留的那片深黯绿色世界的记忆?
二、“夏帝之子”的森林世界
搜寻古代典籍中存留的有关深黯绿色世界的断片记忆,最为荒远的大概要属庖羲氏之前、发明了用火的燧明国了。其国“有火树名燧木,屈盘万识,云雾出于中间。……有鸟若鸮,以口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成(感)焉”[59]。其次会想到的是《史记》的《五帝本纪》,其中记载了五帝之首的黄帝“教熊罴貔貅貙䝙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又谓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和“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60]。太史公之笔令人恍然想到黄帝是一个出入于密林和平野,与猛兽打着交道的氏族首领。同书在叙写五帝的最后一位舜时又有:
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尧以为圣。[61]
能令常人行而即“迷”的“山林川泽”该是多么深黯幽邃?《史记·楚世家》中析父向楚灵王叙述楚之先王熊绎事迹的话,亦让吾人想到农耕文化如何异常艰苦地自山林草莽中被开辟出来:
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王事。[62]
熊绎在位的时间,比公元前一千年稍早,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其时尚被原始密林所覆盖。“筚路蓝缕”和“桃弧棘矢”活现了其自山林世界启建基业的生存环境。在此,自森林辟路而出,如孟子叙述的“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唐尧时代“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63] 一样,是一桩被歌颂的盛举!《国语·吴语》中申胥谏吴王时曾提到楚灵王的一段遭遇,其中有:
其民不忍饥寒之殃,三军叛于干溪。王亲独行,屏营彷徨于山林之中,三日乃见其涓人畴。王呼之曰:“余不食三日矣。”王枕其股以寝于地。王寐,畴枕王以墣而去之。王觉而无见也,乃匍匐将于棘闱。[64]
《吕氏春秋》记有一位术士单豹:
单豹好术,离俗弃尘,不食谷实,不衣芮温,身处山林岩堀以全其生。不尽其年,而虎食之。[65]
与李少君“死于岩石之间,尸为虎狼狐狸之食”[66] 一样,这差不多是伯夷、叔齐采薇首阳山,饥馁而死故事的翻版。
以上所有叙述都将“山林”置于人境之外,令人迷茫和恐惧:舜、熊绎和楚灵王进入山林之中,是作为一段考验和苦难加以叙述的;而“不食谷实,不衣芮温,身处山林岩堀以全其生”的单豹,则因离开了华夏的农业文明,不得不让生命终结于森林之王猛兽之口。
《幽明录》中一则关于汉武帝时代的故事比较特别,它透露出其时人类斧斤如何毁灭古老森林:汉武帝一日在宫殿梁上看到长仅八、九寸的小人,须发皓白,笃老之极。遂召东方朔以问,朔告曰:
其名为“藻兼”,水木之精也。夏巢幽林,冬潜深河。陛下顷日频兴造宫室,斩伐其居,故来诉耳。仰头看屋,而复俯指陛下脚者,足也。愿陛下宫室止于此也。[67]
这条资料异常珍贵,是中国古籍中罕见的谴责人类毁林、要求保护森林的声音。以上这些古籍对森林世界的描述都是在叙写人物时一笔带过,读者须靠想象,方能从“行迷”“屏营彷徨……三日乃见人”“虎”“筚路蓝缕”和“桃弧棘矢”这些细节来展开一幅幅原始密林的景象,的确有点依稀缥缈。能令今人更多也更感性地看到森林的文字,是不避以“荆楚”自称的楚人文学文本。屈原《九章》中一章《涉江》如此书写了诗人进入了“深林”之中: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
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猿狖之所居。
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
霰雪纷其无垠兮,云霏霏而承宇。
哀吾生以无乐兮,幽独处乎山中。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68]
诗人以“杳以冥冥”“蔽日”“幽晦”极力渲染深林的阴暗无光,而这里是他不去“从俗”而“独处”的所在,即人境之外的世界。承袭宋玉《招魂》所开启的将亡魂自地狱般的蛮荒大自然中召回的传统,《大招》中出现了一个地狱般的山林世界:
魂兮无南!
南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
山林险隘,虎豹蜿只;
鰅鳙短狐,王虺骞只。[69]
山林世界的恐怖在此是以恶兽体现的。《招隐士》则对单豹一类隐士离群索居的“深林”环境,做了更为细致的描写:
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兮枝相缭。
山气巃嵸兮石嵯峨,溪谷崭岩兮水曾波。
猿狖群啸兮虎豹嗥,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
坱兮轧,山曲岪,
心淹留兮恫慌忽。
罔兮淴,憭兮栗,虎豹穴。
丛薄深林兮,人上栗。
嵚岑碕礒兮碅磳磈硊,树轮相纠兮林木茷骩。
青莎杂树兮薠草靃靡,白鹿麏麚兮或腾或倚。
状儿崯崯兮峨峨,凄凄兮漇漇。
猕猴兮熊罴,慕类兮以悲。
攀援桂枝兮聊淹留。
虎豹斗兮熊罴咆,禽兽骇兮亡其曹。
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70]
这一段描写,显然是自一身处林中之人的视角,写到“深林”的方方面面:林木枝条间的盘结纠缠,地面落叶和荒草的深厚堆积,山崖的险峻,岩石的崚嶒,野兽的咆哮和追逐,甚至林木中缭绕的“山气”和迷雾的气味……这种描写虽不免想象的成分,却当有相当的身体经验为基础。然而,如《国语》《史记》和《吕氏春秋》等书一样,“山中兮不可以久留”,森林是个应当回避的世界。其总体意象是以“迷”“杳以冥冥”“蔽日”、“幽晦”“山气巃嵸”表现出的阴暗。这种阴暗由草木郁盛、林木枝叶的纠缠,更由人基于未知的恐惧,熊罴虎豹等猛兽的咆哮更渲染着恐怖气氛。
然而,荆楚文学的《九歌》中尚有一篇《山鬼》,它描写了山林,却同时流溢出柔媚之情: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罗。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
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
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
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
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
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
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
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又夜鸣。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71]
“留灵修”和“思公子”的山鬼无疑是一位女神,甚至是巫山神女的化身,然其原型却可能是“夔”或“枭阳”那样形体“仿佛似人”的深山猿狖。[72] 这类动物在林木之间攀援、奔跃,悠荡,须依赖密林而栖息生存,即王夫之所谓“木以蔽形”的“木客”[73]。萧兵注意到:“神农架—巫山—秭归(传说为屈原故乡)这个相邻的三角形地区,猿猴故事、‘野人’传说分外丰富。《九歌》的山鬼以及与她关系密切的巫山神女都极可能以猿猴或‘野人’为原型。”[74] 而这一个三角地区即孕育着荆楚文学。在屈原所生活的公元前4至3世纪,纵然已历经熊绎以来的开辟,然必尚有大片山岭为原始森林所覆盖。《山鬼》对这位女神生存世界的描绘:“处幽篁兮终不见天”,“石磊磊兮葛蔓蔓”,“饮石泉兮荫松柏”以及“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都透露出这是一个竹木深密、猛兽出没的世界。这位“被薜荔兮带女罗”、“辛夷车兮结桂旗”的女神正是这片幽秘世界的化身。在诗人笔下,她风情万种,又因人间爱人爽约而无限幽怨,吾人由此不难体察荆楚初民对山林在畏惧之余,亦不乏眷恋之情。此篇流露的山林之情,在中文文献中非常罕见。
然而,以上尚非那段历史记忆之全部。在讲述以下的故事之前,吾人不妨翻开美国学者埃尔文的《大象的退却——一种中国环境史》这本书,该书有一个重要的观察:
位于以阔叶落叶区南部即黄河河谷中部的经典中国核心文化,对森林没有依恋之情,没有保护森林的责任感……那里曾对山岳和河流常年祭祀,有过这些自然现象的神圣且具魔力的意识。也曾有过神祇掌控风雨的信念。《礼记·月令》中“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也显示了至少最低程度的对森林的崇拜或和解。然而,至少就我所知,在被我们认知为“中国的”最古老地区,没有能被清楚鉴认的森林之神或森林女神。[75]
这位美国学者显然忽略了本文以上援引的《高僧传》中的“夏帝之子”、赤城山神,以及《幽明录》中的藻兼一流山林神怪。但埃尔文的话仍不失为对中国自然崇拜独特性的很好观察。然而,文化人类学却肯认:初民对类似狄安娜(Diana)那样的森林神祇的崇拜是普遍存在的。那么,除却以上那些不够清晰的例子而外,中国的现存文本中是否还留下为追溯更早曾存在这类神祇的线索呢?
不妨从文化人类学的巨著——弗雷泽的《金枝》开始思索。作者自森林祭司或森林之王的命运开始了对巫术的探索。在描述种种林木崇拜之先,像埃尔文的著作一样,弗雷泽也从历史时空的高处鸟瞰曾被森林覆盖的一片广袤大陆:“在历史的黎明期,欧洲曾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所覆盖,在其中散落着的清除了森林的开掘地,恰如小岛在碧海中出现。在我们之前的第一世纪,赫塞尼安森林自莱茵河向东不中断地伸展,一下子就到了未知的所在;西泽询问过的日耳曼人曾在其中旅行了两个月而没有尽头。……”[76] 在这样的地貌背景里,日耳曼最古老的圣殿就是自然森林,所有欧洲初民都被证明曾崇拜林木。同时,类似阿瑞吉亚森林(Grove of Aricia)中发生的故事——为草木世界的新生,森林祭司或森林之王在春夏的特定日子里被杀死或被象征性地杀死,也就成为了处处可见的民俗。弗雷泽列举了一系列在圣灵降临日模仿杀死森林祭司的仪式,其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细节——扮演森林祭司的独特装束,值得吾人留意:
在低地巴伐利亚,树灵Pfingstl从头到脚肿穿戴着树叶和花朵。……帽子以水中的花朵覆盖,且冠以牡丹花束。其上衣的袖口亦以水草编就,其身体的其余部分则以赤杨和榛树的叶子所包裹。[77]
在萨克索尼和泽润根,圣灵日有个被称为“将野人逐出灌木”或”从森林引出野人”的仪式。一位年轻人被以树叶和青苔包裹着,被叫作“野人”。[78]
在波希米亚的色米克,圣灵日也能看到斩首(森林之)王的习俗。……王穿上装饰着花朵的树皮袍子,他的头上戴着插着鲜花和树枝的树皮王冠。[79]
在波希米亚的皮尔森地区的圣灵日,(森林之)王披着树皮,以鲜花和丝带装饰,他头戴金纸的王冠,骑着一匹以鲜花装饰的马。[80]
弗雷泽从森林之王穿戴的树皮、树叶和鲜花推断:这些习俗皆渊源于此书开篇所叙述的故事——在阿瑞吉亚的狄安娜森林持续发生的祭司更新换代的传统。倘若吾人相信弗罗贝纽斯(Leo Probenius)开启的认证文化人类学发现所具的普遍意义,就不得不去思索中国上古时代存在这类习俗的可能。吾人会首先想到山鬼的装扮:“被薜荔兮带女罗……辛夷车兮结桂旗。”然而,更令人发生联想的是《离骚》中一再出现的抒情自我形象,其与草木世界的关联实在太不寻常:“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杂申椒与菌桂兮,岂惟纫夫蕙茝?”,“矫菌桂以纫蕙兮,索胡绳之纚纚”,“擥木根以结茝兮,贯薜荔之落蕊”,“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制芰荷以为衣兮,雧芙蓉以为裳”[81]……人们惯以“香草香花”或“香草美人”来概括以上披戴。然而,《离骚》中常常出现的“木兰”“椒”“菌桂”其实是香木。《南方草木状》言“桂出合浦,生必以高山之巅,冬夏常青。其类自为林,间无杂树”[82]。此外,屈赋中的“琼”“若木”“扶桑”也皆为神话中的树木。当然“留夷”“揭车”“杜衡”是香草,“江离”“芷”“宿莽”则是水泽中的香草。“秋菊”“芙蓉”则是芬芳的花朵。所以,出现在诗人想象中的抒情主人公之披戴,恰如弗雷泽在各地林木崇拜习俗中所观察到的象征草木之灵(spirit of vegetation)的祭司扮演者的装束。当然,屈原诗作只是以此隐喻其芳洁美好的精神质量,并无将自我比同森林之王的意图,诗中亦未出现杀死草木之灵的场面。但诗中一再发出的类似“恐鹈鴂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83] 的呼喊,却同样表达了草木将随时间流逝而凋萎的忧虑。这样一种重复出现的奇特装扮和对凋委季节的敏感,令本人想到:诗人或许是自某种类似弗雷泽观察到的民风习俗中汲取了灵感,尽管这种习俗可能终于日渐式微甚至消失了,诗人不过是如诗中所说“謇吾法夫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84] 罢了。然则,在“夏帝之子”的“深林”与中古的“山水”之间,究竟横亘着怎样一段历史?发生过什么?
三、“去森林化”后的中国山水文化
中国历史地理学者文焕然先生研究七八千年前至今中国境内森林资源分布的变化,认为中国古代曾经“是个多林的国家”,“历史时期中国森林的变迁是巨大的,这与中国‘人与生物圈’的变化,也就是与中国自然环境及人类活动的变迁,是紧密相连的。”[85]文先生依据学界对殷墟甲骨文字的研究、历代文献记载以及古动物化石的研究成果,探讨了了历史动物地理,包括孔雀、扬子鳄、野象、犀牛、大熊猫、野马、野驴、野骆驼和长臂猿的古今变迁,其中以对野象从北纬40º06’不断南迁而终移至24º.6’的历史最为详细。因为“野象分布北界的变迁是中国野生珍稀动物中最大的一个”[86],“气候带的由北向南迁的总趋势(其间有反复)与野象分布北界由北向南迁移的总趋势(其间有反复),有着密切的联系”[87]。文先生将以上植物和动物变迁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气候的从温暖转为寒冷,同时也谈到以铁器和牛耕的推广而得到发展的垦荒活动,在春秋战国以后加速了对植被的破坏。
象是适宜于温暖湿润森林的巨兽,嗜水,需以洗浴降低体温,又不喜阳光曝晒。从殷墟发掘出的象坑、商王曾在沁水和黄河之间猎象的记载、以及曾以象作为祭祀的牺牲[88] 等等事实,今人可以想象上古时代黄河下游地区为茂密的森林覆盖的景象。以此,古人文字中时见的“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89] 或者“舜葬于苍梧下,象为之耕”[90] 就可能并非虚妄之言了。
受文焕然研究成果的沾溉,美国学者埃尔文以《大象的退却——一种中国环境史》一书进一步提出:“大象退却的模式就时间和空间而言,为华夏初民栖居的扩展和强化意象所左右。华夏农耕者与大象从不混杂于一处。……对野兽的战争总地说来是古典中国日后从中出现的周代早期文化之界定性特征。”[91] 比之文焕然,埃尔文显然更强调了人类农业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他提出的时间分界线是公元前10世纪西周开始的为创立中国农耕文明所伴随的“大规模去森林化”(great deforestation)。果然,《诗经·大雅》中被称为“周人史诗”之一的《皇矣》中就有“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启之辟之,其柽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兑”[92]。另一首所谓“周人史诗”,颂扬古公亶父的《绵》中,也有“柞棫拔矣,行道兑矣。混夷駾矣,维其喙矣”[93]。《周颂》《载芟》中亦有“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94]……以农耕立国的周王朝不仅推翻了暴虐的殷商,且经由“柞棫拔矣,行道兑矣”的去森林化而“驱虎豹犀象而远之”[95],开拓出一个“千耦其耘,徂隰徂畛”,畎渎町畦齐整的农耕世界,一个与“狐狸所居,豺狼所嗥”,荆棘未翦的诸戎世界不同的华夏文明世界。这个过程,就是最终向狩猎-采集原始文明告别,森林却正是后者得以存在的环境和象征。而上一节笔者所征引几部史书的作者,包括公元前3世纪的吕不韦、公元前2世纪的司马迁和更早的《国语》作者,皆生活在西周“大规模去森林化”之后的年代里,其时人们已与那个绿色世界疏隔了很久,森林在其笔下故而才是令人迷茫和恐惧的。
“去森林化”是所有农耕文明开始的标志。维柯说:“希腊人开始计算他们的年历,是从赫库勒斯放火焚烧涅米亚森林,用空地来耕种时算起。”[96] 欧洲中世纪对农业耕地的垦拓,同样不免伴随着对森林的砍伐清理。然而,在垦拓农地之后,欧洲尚有为御林法管辖的大片皇家狩猎区以及封建权贵的私人猎园(private park),甚至个体农户的庄园也可能建在林中而成为“林中宅邸”(woodhouse eves)。[97] 正如格拉肯以大量文献所证明的,由于森林对放牧、狩猎、养蜂和防止土壤流失的价值,欧洲中世纪砍伐森林以开垦农地的活动,始终为种种保护森林的法令、法则所限制和平衡:“试图限制这些(砍伐森林)权利的举措几乎与权利本身一样历史悠久。……这两种倾向之间不稳定的休战状态贯穿了整个中世纪。……大的趋势似乎是,这些权利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朝着更精确和划界的方向发展。”[98] 而且,比之中国上古时代的“去森林化”,这种对森林清理的发生年代毕竟要晚的多。对森林的尊崇依然影响着艺术与文学。
对中国山水景观中缺欠森林的现象可以提出各种解释,然最根本的原因应当是:这已经是一片太早经历了更彻底的“去森林化”而建立起了农耕文明的土地。其比之欧洲文明告别森林生活的历史更久远,以致自然崇拜中已没有了森林神祇,以致在平野之上已难见到森林,[99] 以致农田或已开垦到了山岭之上,以致东晋以后士人游赏和吟咏大自然时,“山水”才是美景。
“山水”这个汉语中的新语词是伴随士人开始游赏山水在公元4世纪的东晋出现的。它既为意义相对的单字之并列式构词,本身暗示了一种“一元双极”之“完形”,是“山”“水”以转喻形式实现的词义扩大,并山与水的相对并列为其基本构架。[100] 当然,被历代视为山水诗开山人物的谢灵运(385—433)在游山时也会时而面对深秘的原始森林,《宋书》本传甚而谓其“尝自始宁南山伐木开径,直至临海”[101]。灵运诗作中故而也出现了“荒林”“密林”“长林”“疏木”“群木”“乔木”“林迥”“林深”“林壑”等等意象。然而,森林的书写远未取得山与水在话语中的凸显位置,而且他并未去进入森林内部去观察。从其所撰《游名山志》《山居赋》看,其所居所游之处并非没有森林,但诗人对森林却欠缺一份特别的憧憬之情。
正是因对那个猛兽出没、林木郁暗的蛮荒世界已丧失憧憬之情,在后世诗人笔下,它才甚而沦为了唤不起美感的地狱意象。柳宗元的《囚山赋》是这样书写山林的:
沓云雨而渍厚土兮,蒸郁勃其腥臊。阳不舒以拥隔兮,群阴冱而为曹。……攒林麓以为丛棘兮,虎豹咆㘎代狴牢之犬嗥。胡井眢以管视兮,穷坎险其焉逃?顾幽昧之罪加兮,虽圣犹病夫嗷嗷。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102]
山林已成为囚牢,成为生命须承受折磨的所在。然而,如此猛兽相号、丛棘满目的山林,却非主要出自诗人的身体体验,而是全然取自楚辞《招隐士》以及《招魂》《大招》等文本语码的纯粹“符号的风景”(semiotic landscape)。[103]
却除了林中视野、以山与水的相对并列为自然景观的基本构架,中国式自然景观的本质就是一种远景、大景。即郭熙所谓:
山水,大物也。人之看者,须远而观之,方见得一障山川之形势气象。[104]
当然,论所谓“山水”,文人所偏爱的其实是青山绿水,即覆盖着竹树植被之山和自因覆以植被而水土保持尚好的山中流下之水。中国诗画写山多写烟云,乃至谓“画家之妙,全在烟云变灭中”[105],而烟云须依赖林木而生。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诗人画家要深入林中,从林木遮蔽的深林中取景。相反,他们多是自深林之外去望山看水,中国诗画中的山水,故而亦率皆倡“远”。
唐君毅谓“远”是“山水形质的延伸”,并以为其意义须当追溯至魏晋玄学。[106] 玄学诗哲嵇叔夜有诗曰:
流磻平皐,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107]
这是最典型的远境,所咏乃在平皐长川,地远天高。此一个“远”,须以了无遮蔽的视野为前提。为自反面说明这一点,笔者不妨摘引一段从文化人类学研究风景的学者对亚马逊景色的描述:
对于来自温和气候地区的人而言,亚马逊很难被视作风景。大地不会从一个视点到遥远地平在线退却,因为处处林木都阻断了视线,目光只能穿越一小段距离就没入了密集的树木。沿着大河,你能看得更远,但即便在此也没有遥远的蓝色地平线。天空自森林的屏幕后陡然出现。视野被包围着,倘若不是一个平地上旅行或者有许多天的路途了解这些大河之地的规模和无边际的森林,你将坠入幽闭恐惧之中。在亚马逊的大部分地区旅行,都是穿越于不停连续展开的小块封闭地方之中,并令想象力从中建造出无限量空间之伸延。只有当亚马逊景色被道路和去森林化急剧转变之时,它才展现为一个视野能伸展的空间。一条明亮的红色道路伸向地平线,而建筑、篱笆和孤立的树木则推向远方。它更像温和的北方风景,其中树林不再统治着视野,而只是大地和远方天空之间的模糊过渡。[108]
这段文字不是很好地说明了没有森林遮蔽对风景中“远”是多么重要么?画道倡远。郭熙首论“山有三远”,其中“自山下而仰山巅”的“高远”以及“自近山而望远山”的“平远”,显然不可能发生在密枝繁叶的林中。即便视点可以移动,亦须沿未有林木遮蔽的空间。而“自山前而窥山后”的“深远”[109],必亦令望眼越过重岩疏木一段纵深而至山后,以清人费汉源之说,“深远者,于山后凹处染出峰峦,重叠数层者是也。……要使人望之,莫穷其际,不知其为几千万重”[110]。这也是不可能自林中展开的透视。至于宋人韩拙提出的“阔远”“迷远”和“幽远”则更与林中视野无缘:“阔远”之“有近岸远水,旷阔遥山者”须是隔水而骋目于对岸群山众峦之间;“迷远”之“有烟雾暝漠,野水隔而仿佛不见者”是纵目于对岸云天岚光;“幽远”之“景物至绝而微茫缥缈者”[111] 是令目光灭没于浮云杳霭、有无之间。韩拙此“三远”皆是无林木障目面对无际长天的视野。
诗道亦倡远。王昌龄论作诗取景而曰“至晚间,气霭未起,阳气稍歇,万物澄静,遥目此乃堪用”[112],戴叔伦论“诗家之景”当如“如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也”[113],王士祯谓“余尝闻荆浩论山水而悟诗家三昧,其言曰: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114],都在宣说一个“远”字。诗家景中,“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是高远,“威纡距遥甸,巉岩带远天”是平远,“蒸岚相澒洞,表里忽通透”是深远,“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是阔远,“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是迷远,“海门深不见,浦树远含滋”是幽远……所有的“远”都指向一片无林木蔽目的空间。
最后,中国自然风景鉴赏既已不是真正以蛮野意义上的大自然为对象,山水和田园纵有若干不同,即前者比之后者更彰显偶然和不设局格、无方无体,然自根本而言,却又皆为农耕文明中仕宦之外的世界。故“田园诗人”陶渊明亦有《游斜川》一诗写其“临长流,望曾城”[115],而“山水诗人”谢灵运亦不仅撰《山居赋》详说其剡水东岸南北庄园并统“叙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116]。其诗《田南树园激流植援》则不得不归在田园题下了,诗中曰:
中园屏氛杂,清旷招远风。卜室倚北阜,启扉面南江。激涧代汲井,插槿当列墉。群木既罗户,众山亦对窗。靡迤趋下田,迢递瞰高峰。寡欲不期劳,即事罕人功。唯开蒋生径,永怀求羊踪。[117]
在盛唐,此农耕文明之中、仕宦之外的两个世界终于在一群诗人中融而为一,因为二者本皆自农耕文明之根而生。倘以文化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譬喻,二者皆非未经烹饪的“生食”,而是业已烹饪过的半“熟食”了。[118] 由于大规模的“去森林化”及其对于文化心理的影响,后代已再难经由森林这个“中介”,去真正回归“夏帝之子”的世界,回归真正野性意义的大自然了。而在欧洲绘画和文学作品中一再出现的森林意象,却在昭示其对野性大自然仍不乏向往之情。因为正如托马斯(Keith Thomas)注意到的,野蛮(savage)的拉丁词根就是林地(silva),人类是从森林走出而来到文明时代的。[119] 大量文化人类学报告显示:那些处在文明初期的人类部落成年礼仪式中,总有一个黑夜里将少年送入森林独处后再回归部落的环节,以演绎自死亡而再生,自野蛮而文明的故事。在此,青春启悟仪式在重演神话中的宇宙和文明开辟,或者说,“创世纪充当着人形成的模式”[120]。森林是野性大自然的意象。
四、结论
以对照中西绘画和文学对森林之不同态度为基点,本文提出了中古山水艺文研究中一个被忽略的事实:除非为书写入山修炼的释子道士,晋宋以后兴起的“山水”艺文中是鲜见以林中人的视野对森林做描写的。在中国历史地理和环境史两位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本文在追溯了上古文献之后强调:中古艺文中出现的“山水”是以为建立农耕文明的大规模的“去森林化”一千多年以后发生的文化现象。恰如著名地理学者格拉肯所说:“森林砍伐比前工业化社会中任何其他做法都更大地改变了生态系统和陆地面貌。”[121]以山与水相对和并列为中国景观基本构架其实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山水”概括着森林之外“大物”景象的开阔,而山水诗画理论所倡的“远”实乃“山水形质之延伸”。同时,“山水”意味着它已然不是文化人类学者所说的“生食”,而是“熟食”或半熟食。中国文人已不再可能经森林这个中介,去真正憧憬野性的大自然了。故而,“山水”与“田园”结伍,同为仕宦之外的农耕文明世界。
[1] Natural History, 转引自Charles Watkins, Trees, Woods and Forests: A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中译本查尔斯·沃特金斯:《人与树:一部社会文化史》,王扬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8,第10页。
[2] 郭熙:《林泉高致》,载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第67页。
[3] 同上书,第70页。
[4] 韩拙:《山水纯全集》,载沈子丞编《历代论画名著汇编》,第139—139页。
[5] 见David H. Engel, Creating a Chinese Garden (London: Timber Press, 1986), p. 5。
[6] 鲍照:《登庐山》,载钱仲联等增补集说校《鲍参军集注》,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第122页。
[7] 同上书,第124页。
[8] 同上书,第125页。
[9] 曹融南校注集说《谢宣城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233,240页。
[10] 江淹:《江淹集校注》,俞绍初、张亚新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第70页。
[11] 李白:《自巴东舟行经瞿塘峡登巫山最高峰晚还题壁》,载王琦注《李太白全集李白全集校》,北京:中华书局,2015,第1191页。
[12] 韩愈:《南山诗》,载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433页。
[13] 同上书,第433—434页。
[14] 欧阳修、宋祈:《新唐书》卷二百二十五下第20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第6454页。
[15]《江淹集校注》,第49—51页。
[16] 杜甫:《铁堂峡》,载仇兆鳌注《杜诗详注》卷八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2012,第677页。
[17] 杜甫:《青羊峡》,同上书,第684页。
[18] 杜甫:《木皮岭》,同上书,第707—708页。
[19] 杜甫:《飞仙阁》,同上书,第712页。
[20] 何逊:《渡连圻二首其一》,载刘畅、刘国珺注《何逊集注 阴铿集注》,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第60页。
[21] 杜甫:《大历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凡四十韵》,载《杜诗详注》卷二十一第4册,第1867页。
[22] 江淹:《赤亭渚》,《江淹集校注》,第49页。
[23] 何逊:《日夕出富阳浦口和朗公诗》,《阴铿集注 何逊集注》,第105页。
[24] 孟浩然:《渡扬子江》,载佟培基笺注《孟浩然诗集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第424页。
[25] 韦应物:《寄全椒山中道士》,载孙望编《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02,第363页。
[26] 陶渊明:《饮酒二十首(其四)》,载龚斌校笺《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第219页。
[27] 陶渊明:《归园田居五首(其一)》,同上书,第73页。
[28] 王绩:《田家三首》,《全唐诗》卷三十七第2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第478—479页。
[29] 孟浩然:《涧南即事贻皎上人》,《孟浩然诗集笺注》,第337页。
[30] 萧驰:《诗与它的山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第235—244页。
[31] 王维:《归嵩山作》,载陈铁民校注《王维集校注》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108页。
[32] 王维:《淇上即事田园》,同上书,第77页。
[33] 王维:《辋川闲居赠裴秀才迪》,同上书,第2册,第429页。
[34] 孟浩然:《樵采作》,《孟浩然诗集笺注》,第329页。
[35] 王维:《辋川集·斤竹岭》,《王维集校注》第2册,第416页。
[36] 欧洲风景绘画中森林是经常用的题材,让读者想到荷兰画家凯力克斯(Alexander Keirincx)的《猎鹿》(Stag Hunt)、萨夫特列文(Herman Saftleven)的《森林内景》(Interior of a Forest);英国画家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的《有池塘的森林风景》(Wooded Landscape with Pool)、康斯太勃尔(John Constable)的《森林边缘》(Edge of a Wood)、威尔逊(Richard Wilson)的《孤寂》(Solitude)和法国画家巴比松画家柯罗(Camille Corot)的《枫丹白露森林》(Forest of Fontainebleau)、迪亚兹·德拉佩纳(Narcisse Virgile Diaz de la Peña)的《林间小溪》、《枫丹白露森林》等等数不清的作品;奥地利风景画家瓦尔德米勒(Ferdinand Georg WaldmÜller)更以一个系列描绘了维也纳森林在四季晨昏间的不同景色。
[37] 维柯:《新科学》,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第451—454页。
[38] 查尔斯·沃特金斯:《人与树:一部社会文化史》,第24页。
[39] Corinne Saunders, The Forest of Medieval Romance: Avernus, Boceliande, Arden (Woodbridge, 1993), p.10.
[40] 见Northrop Frye, Fables of Identity: Studies in Poetic Mythology (New York: A Harvest/HBJ Books, 1963), p. 20。
[41] 见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82-183。
[42] 见《旧约·创世纪》第2章。
[43] 《谢灵运集校注》,顾绍柏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第174,178,183页。
[44] 谢灵运:《山居赋》,同上书,第327页。
[45] 同上书,第328页。
[46] 见萧驰:《诗与它的山河》,第90页。
[47] 谢灵运:《临终》,《谢灵运集校注》,第204页。
[48] 释慧皎:《高僧传》卷十一,汤用彤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第402页。
[49] 同上书,第403—404页。
[50] 同上书,第407页。
[51] 同上书,第408页。
[52] 同上书,第417页。
[53] 同上书,卷四,第163页。
[54] 支遁:《咏禅思道人》,载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1083页。
[55] 支遁:《咏怀五首(其三)》,同上书,第1081页。
[56] 同上书,第329页。
[57] 江淹:《杂三言五首》其四《悦曲池》,其五《爱远山》,《江淹集校注》,第78—79页。
[58] 闻一多:《道教的精神》,载《闻一多全集》第1册,第143—145页。
[59] 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四部丛刊三编影印本,引自《王子年拾遗录》卷八六九,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第2页。
[60] 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卷一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63,第3—6页。
[61] 同上书,第22页。
[62] 《史记·楚世家》,《史记》卷四十第5册,第1705页。
[63] 《孟子·滕文公上》,引自《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2705页。
[64] 《国语·吴语》,引自仇利萍校注《国语通释》,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第636页。
[65] 《吕氏春秋》卷十四《孝行览》,收入《诸子集成》第6册,上海:上海书局,1987,第157页。
[66] 《论衡·道虚篇》,收入《诸子集成》第7册,第71—72页。
[67] 《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王根林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第695页。
[68] 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130—131页。
[69] 同上书,第217页。
[70] 同上书,第232—234页。
[71] 同上书,第79—81页。
[72] 见萧兵:《夔枭阳·野人·巫山神女》,载《楚辞新探》,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第410—424页。
[73] 王夫之:《楚辞通释》,《船山全书》第14册,长沙:岳麓书社,1996,第269页。
[74] 《夔枭阳·野人·巫山神女》,第425页。
[75] 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Elephants: An Environmental History of Chin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46.
[76] James G.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The Roots of Religion and Folklore(1890 version, two volumes in one)(New York: Avenel Books, 1981), pp. 56-57.
[77] Ibid, p. 242.
[78] Ibid, p. 243.
[79] Ibid, pp. 244-245.
[80] Ibid, p. 246.
[81] 《楚辞补注》,第4-41页。
[82] 《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卷中《南方草木状》,第260页。
[83] 《楚辞补注》,第39页。
[84] 《离骚》,《楚辞补注》,第13页。
[85] 文焕然:《中国森林资源分布的历史概况》,载文榕生选编《中国历史时期植物与动物变迁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第3—14页。
[86] 文焕然:《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初步研究》,同上书,第199页。
[87] 文焕然:《再探历史时期中国野象的变迁》,同上书,第212页。
[88] 见王宇信、杨宝成:《殷墟象坑和“殷人服象”的再探讨》,载胡厚宣等《甲骨文探史录》,北京:三联书店1982。
[89] 《淮南子·墬形训》,收入《诸子集成》第3册,高诱注《淮南子注》,第58页。
[90] 《论衡·书虚》,收入《诸子集成》第7册,第36页。
[91] Mark Elvin, The Retreat of Elephants, pp. 9-11.
[92] 《大雅·皇矣》,引自孔颖达《毛诗正义》卷十六,《十三经注疏》,第519—520页。
[93] 《大雅·绵》,同上书,第511页。
[94] 《毛诗正义》卷十九,同上书,第601页。
[95] 《孟子·滕文公下》,引自《孟子注疏》,《十三经注疏》下册,第2714页。
[96] 维柯:《新科学》,第159页。
[97] 英国的例子见W. G. Hoskins的名著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Landscape, 中译本见《英格兰景观的形成》,梅雪芹、刘梦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第86—94页。
[98] 见Clarence J. Glacken, Traces on the Rhodian Shore: Nature and Culture in Western Thought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End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p.329。中译本见《罗得岛海岸的痕迹:古代到十八世纪末西方思想中的自然与文化》,梅小侃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第323页。格拉肯的举证包括查理曼大帝的《庄园村镇法令》第36章、日耳曼国王阿尔伯特一世和亨利七世1289年的法令、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1331年有关佩格尼茨河两岸和王室森林法令、班贝格主教的1328年保护主教辖区森林的法规等等。
[99] 埃尔文以《左传》宣公十二年中“赵旃弃车而走林”和成公二年中“骖絓于木而止”等三条记载为据,说明公元前6世纪时驷马两轮的车乘,是不可能驰骋于生长森林的平野上的。见Elvin, The Retreat of the Elephants, pp. 44-45。
[100] 见萧驰:《从实地山水到话语山水——谢灵运山水美感之考掘》,《中国文哲研究集刊》2010年第37期,第1—50页。此文的修正版见萧驰:《诗与它的山河》,第47—130页。
[101] 沈约:《宋书》第6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第1775页。
[102] 同上书,卷二,第63—64页。
[103] 见Kalevi Kull, “Semiotics of Landscape,”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Landscape Studies, eds. Peter Howard, Ian Thomson & Emma Waterton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p. 98-102。
[104] 郭熙:《林泉高致》,第65页。
[105] 莫是龙:《画说》,《历代论画名著汇编》,第213页。
[106] 唐君毅:《中国艺术精神》,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第299—302页。
[107] 嵇康:《兄秀才公穆入军赠诗十九首(其十五)》,《嵇康集校注》,戴明扬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第15—16页。
[108] Peter Gow, “Land, People, and Paper in Western Amazonia,” in The Anthropology of Landscape: Perspectives on Place and Space, eds Eric Hirsch and Michael O’Hanlon (Oxford: Claredon Press, 1995), p. 43.
[109] 郭熙:《林泉高致》,第71页。
[110] 费汉源:《山水画式》,载俞剑华编《中国画论类编》,香港:中华书局,1973,第838页。
[111] 韩拙:《山水纯全集》,《历代论画名著汇编》,第135页。
[112] 王昌龄:《诗格》,《全唐五代诗格彚考》,张伯伟彚考,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第169页。
[113] 引自司空图:《与极浦书》,载郭绍虞、王文生编《中国历代文论选》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第201页。
[114] 王士祯:《带经堂诗话》卷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86页。
[115] 《陶渊明集校笺》,第84页。
[116] 《山居赋》,《谢灵运集校注》,第319页。
[117] 《谢灵运集校注》,第114页。
[118] 列维·斯特劳斯(或译作李维史陀)这一观念,详见其《神话学:生食和熟食》,周昌忠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第87—90页。
[119] 基思·托马斯:《人类与自然世界:1500—1800年间英国观念的变化》,宋丽丽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9,第197—200页。
[120] Mircea Eliade, Myths, Dreams, and Mysteries: the Encounter between Contemporary Faiths and Archaic Realities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1960), pp. 193-197.
[121] 《罗得岛海岸的痕迹》,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