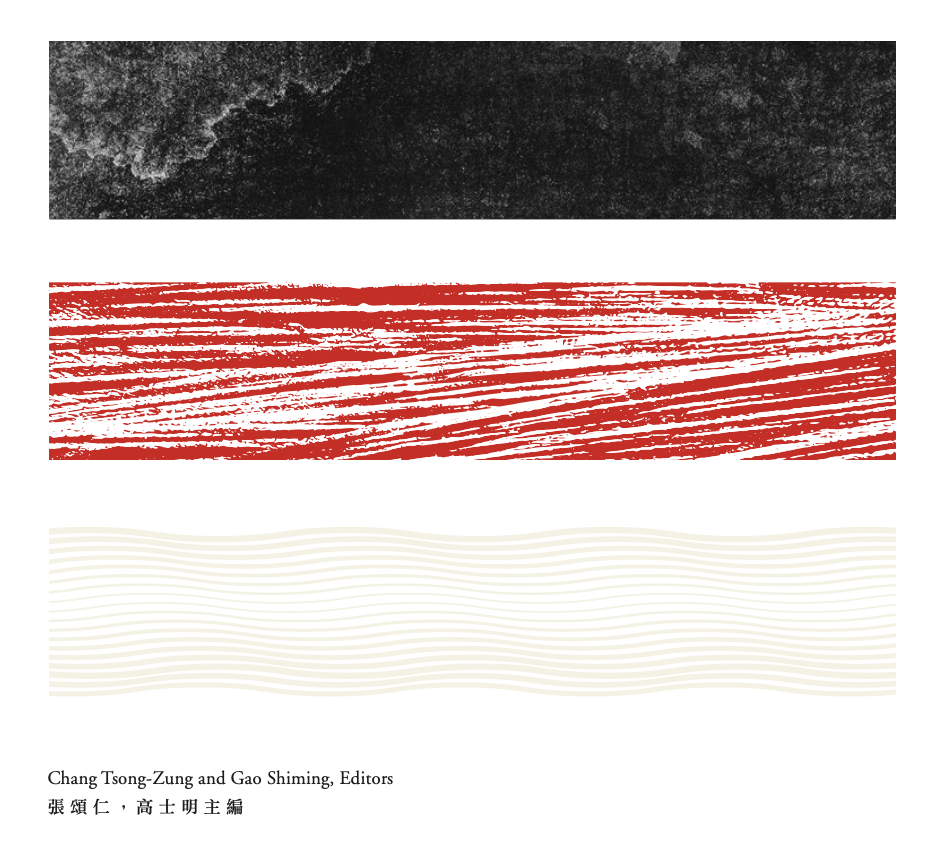2013
“汉雅一百:偏好”汉雅三十年庆之“三个艺术世界”论坛发言稿
一
画在拉斯科岩洞石壁上的马儿,已向我们证明,艺术作品能被保存到永远,超出历史谱系,久过美术馆、博物馆、纸、布、皮、墨、色本身的物质寿命。
艺术本身就是保存行为。艺术本身,而不是人的算计和操持,才是保存的最好方式。最好的艺术收藏,也只是使收藏行为本身成为艺术行动,任作品里的艺术,自己去保存自己到永远。最高等级的收藏行为,是自己成为一个艺术行动,不用人为支持地让自己保存到永远。
收藏行为的最根本姿态,是这种:让,任……
二
哲学家吉尔·德勒兹说,艺术是要去保存作品里的感块(affect)和知块(percept)了,而它也是这世界上唯一能自我保存的东西。它保存,并在它自身之上自我保存。这句话强调:艺术是“唯一能自我保存”下去的东西,连收藏这一手段,也不算添助,还不够,自己保存不了自己;收藏行为也必须先成为艺术行动,才能让自己不依赖于任何手段,像艺术那样地去永远地自我保存。
看来,并不需要我们拿出专门的套路、格式和技术,去保存艺术,而是反过来,先去成全艺术,顺着它的自我保存,去保存它;它是:帮那能够自我保存的艺术去自我保存。收藏这一行为的唯一目标,是成为艺术那样的行为,化身于艺术这一最大的保存行为之中。收藏,然后保存,然后流传,到了最后,就只有艺术,没有收藏和收藏者,没有作者,也不依赖于画框和画布了:“瞧,这个姿势,这年轻姑娘在那里已摆了五千年的姿势了,已不再依赖于谁画出它,谁来看了。是艺术将这个姑娘的这个姿势,保存到了永远。”
保存艺术作品,是为了保存作品内的另外的东西(“作品”只是一个框)。这另外的东西是什么?它是那能够自我保存的东西。德勒兹说:“[……]自我保存下来的东西,物或艺术作品,是感性的一块,保存下来的,是感块和知块的合成。”[1] 用艺术去保存,是从我们的感性、知觉和观点中抽离出感块和知块,后者才能够永远自我保存下去,能流传的,只是这些块块。
做艺术是要保存,做收藏是要通过先成为艺术,艺术地去保存,然后艺术地去保存那自己就会去保存的东西,留下来,真正能流传的,是那些感块和知块,后者并不依赖于我们的美术馆和博物馆,甚至其寿命都将远超出我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经济制度,像在岩洞石壁上的原始绘画上的那些块块一样,一直坚挺到今天。
最终,以长焦距看,做收藏和做艺术,是在做同一回事:保存,更大意义、程度上的保存(下文我们将讨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生存论意义上的“保存”)。做艺术收藏,是要比共同体、社会和时代所要求的还更长久地去保存,是要比共同体、社会和时代更长久、超过它们本身的寿命地去保存那些留下的感块和知块……
那也就是说,最高等级的收藏,是艺术,是保存,是要比我们时代的美术馆更可靠地使我们时代的收藏成为艺术,并利用这种艺术的自我保存,来保存我们的所保存,使之流传,挺持、残存、挥之不去……
三
在《历史哲学论纲》中,瓦尔特·本雅明向我们指出,过去的真正图像(das wahre Bild)(过去作为一片片图像?来自过去的一片片图像?过去本身作为一片片图像?),正飞快地飘离我们。而过去只有作为图像,才为我们所把握。它总在可被我们认识的那一刻弹出,旋即湮没……过去的图像一旦不能成为当前的关怀,被我们认出,就将永远不可追回。图像并不是过去在当前打下的烙印,或者是当前在过去投下的阴影;图像是那已经存在过的东西,在某一闪忽中,与当前结合了,是过去与当前形成的一个星丛或聚合(constellation)。[2] 在图像中,过去和当前在某一瞬间里连接、聚合,在其中,当前才能够认出过去的意义,过去也在当前中寻找到了它的意义和完成。图像是某个过去与当前的联合。
由此看,一切过去的艺术作品,可以说都是当代艺术作品;展览的使命,是使过去的一切艺术作品在今天仍然成为艺术作品,使古画、近画和今画重合。收藏来自过去的图像,是将它们汇合在当前的时间刻度上。站在当代,或以当代艺术的态度,去接受来自过去的图像,这就是收藏了。
收藏是尊重图像自身的方式,将过去引用到当前。通过引用,过去的许多代人,才与当代人之间有了神秘的相遇。是引用牵了线。本雅明指出,引用不在于保留,而在于毁坏:引用通过叫出其名字,而将字和画叫到我们眼前,毁灭性地将字和画从它的上下文里攥出来,但正因此,也将它唤回根源;引用在拯救的同时,也加以惩罚。(《历史哲学论题》)在《什么是史诗剧》里(《选集》,第151页),他说,引用是对上下文的打断。破坏了上下文,引用才能成功。引用是救赎,是要将字和画,从过去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引用而不加引号,才是真正的救赎:引用一成功,弥赛亚就降临。而收藏是不成功的引用。它也是暴力的引用。
今天要借助收藏行为,是因为,我们越来越不善于引用了。本雅明说:“就如我们之前的好几代人那样,我们被赋予越来越弱的弥赛亚力量。”这样说,不是悲观。他接着说,病弱、责难、必然性、迫害和绝望,反而会使弥赛亚早日降临。我们的收藏行为越来越弱,越来越不自信,但这反而会促使我们引用得更迫切,被救赎得更快些。收藏是迫不及待和不顾一切的引用。
引用或收藏(作者和艺术家其实都是很好的引用者或收藏家),活像埋伏在路边的强盗,用刀逼着路人,要抢走他们的确信。当代人没了确信,才去抢劫过去的作者的确信?收藏,是在猎取前代人的“确信”?在本雅明看来,过去只是被割掉了上下文,破坏了,才放到我眼前的。过去只有被一种异化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当前的收藏)攫住,才可见。那一过去,只有在这样的被异化、被毁灭的瞬间,才露脸。就像在大的危险中,某种记忆才惊艳地闪现。直白地说,过去的字和画,也必须在被当代人抢劫,也就是说被引用和收藏之后,才露脸。到这里,本雅明露出了他对收藏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收藏了,被粗暴地引用,被不法地征用和没收之后,历史作品才有机会露脸,才会得到有利的评价。
本雅明眼中的收藏家,是一个将作品拖出去,毁除它的上下文关联,将其紧紧搂在怀里的人。他们引用,由此而夺走作品或商品的使用价值,或社会-伦理意义。作品的正宗与否,是由作品和商品被这样引用之后产生的异化的大小来衡量:越正宗,它被异化得就越严重。越收藏,就越异化。我们评价一个被收藏的作品,是看它与我们今天、当前的历史境遇的相异程度,来定其价值和意义。越与我们本时代相异,被收藏作品就越伟大吗?拿出旧东西,本身也就是在排挤、架空新东西?
这么说,收藏家与革命家的角色相辅相成。对于革命家,新东西的出现,必须以毁灭旧东西为前提。所以,在传统社会的稳定秩序里,引用和收藏,是不大可能的。只有在与传统的决裂期,和毁坏后的复兴期,收藏和引用才又兴盛起来。在我们今天这样新和旧、全球和本地脱节的离异时代里,收藏也极度活跃了。收藏促进了各种各样的“换手”,这一道道的换手,更促进了收藏?对于作品,这是一个颠沛游离的时代,对于收藏者,却是一个如鱼得水和游刃有余的时代。下面我们将看到,张颂仁的艺术收藏,却发生在三个时代的汇合、平行处。
四
对于艺术作品收藏家,中国大陆的20世纪,是一个乾坤大挪移的时地。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冷战景观式分离与合并,将人类的各种历史时空挤进同一个世纪中。
而身处中国香港的张颂仁,像蝴蝶一样,采集着其中的花粉。2014年1月18日开展的“汉雅一百:偏好”大展,就是他自己的“中国20世纪”!正如策展人高世名所说,这个展览收容了“中国传统艺术世界、中国社会主义艺术世界和全球资本主义艺术世界三种艺术生产和艺术机制”,汇合了中国古典艺术、民国艺术、革命时代艺术和后八九艺术运动。刘大鸿的《祭坛》,方增先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和陆俨少的《山水》,被放到了同一个时空里,同一个展览装置内,像一坛新酿的百年陈的黄酒:近、现、当代被“吊”到了同一种20世纪的“味”中。
五
要成为艺术作品,一个制品须被切断其文化传承,献祭给一个展览空间。为了艺术而艺术,艺术家须杜绝引用这个时代。现代艺术切断了我们与过去的联系;过去作为废墟越积越多,而我们越来越掉进当前的深渊里。只有拯救,才能打捞这高堆的废墟一样的过去或传统,但在弥赛亚到来前,这又是无望的。文化,我们不要;过去,也只剩其文化价值了。我们要用艺术另找和另搞。像在谷堆前饿昏过去的天使,在等待救赎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什么依仗,只有手里捧着的艺术作品这一道具了。一切都在从我们指间滑去,留在手上的唯有艺术这一保存手段了。
我们无法保存整个过去,收藏是我们不顾历史和文化脉络地去引用的姿态。引用或收藏,本身是一种毁灭式暴力,是要切断艺术品与过去、传统的全部联系,不顾一切地将遗物挪用到当前。过去和传统只是堆积的垃圾,作品无法在这样传述的废墟堆里重新得到权威的支撑。这时,只有收藏家,才会站出来干预,成为艺术品之意义和价值的庇护人。有如此多的艺术品沦为无处安放的碎片,收藏家就担起了一种假托的权威下的庇护责任,使艺术作品在无历史、无传统或传统和历史停滞或搁浅的时代里,有一个人工支撑的档案意义的来源。
这是收藏的要害:在并不清楚地知道那最终被保存到、流传到永久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之前,收藏家就必须出手。这一冒险举动,短期的,称作艺术,长期的,称作收藏。收藏家必须站到比艺术家、艺术史、文明史更高远的立场上,去作出保存的姿态。
在〈爱德华·富克斯:收藏家和历史学家〉(Eduard Fuchs: Collector and Historian,1937)一文中,本雅明指出,富克斯的最大的收藏功绩,或许就在于他“披荆斩棘,将艺术史从我们对大师名字的拜物中解放出来”。伟大收藏家必须“观察那些人们根本看不起、离经叛道的事物,那正是他(或她)的真正长处”。他们必须抱有真正的宽容,和长距离的眼光,执行西西弗斯式的苦劳:通过占有,来脱去物的商品特性。可他们这样辛苦,也只为了赋予物以鉴赏家眼里的价值,并不能给物重新带去使用价值。可他们梦想的,恰恰是进到远古或失去的世界,还想进到一个更好的世界里。他们想要这样一个世界:人们并没有被赋予比日常世界所需更多的东西,在其中,物都摆脱了必须有用这一苦役,所有物品都找到了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角色。[3]
这种收集的姿态,正是哲学家乔吉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亵渎”:通过收藏后重新展出,将(艺术)商品从流通的苦役中解放出来,放入共同体的全新的集体使用之中。究底看,收藏家要解放商品于苦役,解放人于其消费。对市场而言,收藏艺术作品,是使像陀螺一样陷于流通和交易的艺术商品,重新成为艺术品,通过新的展出,以新的形象,亮相公众之前。收藏家在当代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任务,那就是:不要使艺术作品泛滥,通过收藏,使当今的艺术作品能以正常速度流通,这类似于中央银行的回收流动性。
我们引用,是为了利用作品的权威。但我们的引用,又会毁坏被引用的东西的上下文,因而破坏了其出处、身份的权威性。在我们时代,艺术作品失去了它的通过权属于某一传统、某一地点、某一源头而携带的权威性。作品的正宗不正宗,如今已只成了复制得好不好的问题。原作不原作,正宗不正宗,是由市场和媒体来担保了。“做旧”的技术总有一天会压倒专家鉴定的权威。这种百分百的复制,这种所谓的山寨,表面上看是对收藏的毁灭性打击,但在本雅明看来,也是好事:一、技术复制比原作的手工制作更可靠;二、技术复制使原作能存活于更多的地方,其幸存概率大增。典型的例子就是摄影:更好的复制,才能达到更好的收藏。[4]
从此,艺术作品再也不能依靠传统和权威来获得意义,而只能从收藏者那里去寻求庇护和保值。艺术史也成了一道不合缝的篱笆。文化成了垃圾焚烧场。一切艺术作品的命运,都须在收藏者手里了断。全部的艺术史,将断送在他们手里。劫后余生的艺术品,也全要他们的收留,来苦撑出自己的意义。收藏家是艺术的未来法人。我们至今还远远没有了解美术馆对于艺术和艺术作品的全部意义,在此之前,我们请收藏家先代理着美术馆的未来功能。
六
这样的局面,并不是哲学的断想,而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到了中国的20世纪!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张颂仁幸运地撞上了它!我们不难发现,他手里拿着它的总谱。不由得要妒忌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他像激动的孩子那样,抖着手告诉我们:我看见了,我看清楚了,有好多样,我取舍不了,都留下来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拿它们如何是好,那就先存而勿论吧!
张颂仁的汉雅轩,说起来,就是一个中国大陆20世纪馆。因为我们的民族历史叙述在20世纪,被世界历史事件挤爆了,或者说,我们突然有了三种以上的平行历史,或者说,我们把历史当宣传,伪造历史上了瘾,副本太多,找不回源初了。因此,这个20世纪馆就重要了。
这么说,是因为,艺术作品比起其他档案,更好地见证了20世纪的中国。电影导演戈达尔就认为,拍20世纪的电影史,能拍得比写出的20世纪的历史更真,因为,电影见证了它。拍这种见证,比直接去拍历史,会更真实。戈达尔认为,20世纪的电影史,是电影的沉沦史,而这一史,比20世纪历史,更能说明人类在这一世纪中的遭遇。他这强调的是艺术作品的“见证”能力。爱森斯坦也指出,电影里的十月革命比现实里的、历史叙述中的十月革命,要更真实。
那么,汉雅轩给我们保留着怎样的一个中国20世纪呢?
七
“汉雅轩”成立三十周年了。张颂仁的艺术收藏家位置,仍待重估。他对自己的收藏家身份,也继续三心二意。对他所收藏的主要作品的跨年,也就是中国的20世纪,他至今仍抱暧昧态度。他好淡定。
在美国受过精英教育,旁观了中国的革命和后革命,他至今仍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督教和汉族礼教三者之间走着跳棋,或者说,举棋而不定着。不过,可以想见,他理解西方越多,似乎越认准了这一点:做中国人这件事,必须整顿了!他要“复辟”的,是中国人原来行事、设论和立命的简单、沉着和管用。
张颂仁理解的“艺术”,在我看来,是更宽广的一种象征活动,是礼器加仪式。他想要恢复的,是礼器与生活、艺术与共同体之间的更本真的关系。他等待的是将要到来的人民,而不是我们原来有过的生活,或我们过去所沉浸的生活之艺术。艺术作品必须抹煞自己,成为生活必需品,那个人民才会到来。他的这种态度,译成康德、席勒或马拉美后的美学语言,可以表达成:艺术必须成为“生活的艺术”,帮我们过渡到共同体新的感性域,超越有文化的阶级的精致,与没文化的阶级的朴素天性之间的对立。艺术作品通向个人与共同体的新的生活,不光是民族的自身成就,更成为对新人类的许诺。希望这次的“汉雅一百:偏好”展能使作为收藏家的张颂仁更坚信,艺术作品不光能保存一个世纪的迭宕的频谱轨迹,更是激励人民的生活之艺术的全新“礼器”。
艺术比政治更擅长推动新的人类共同体的建立,不是通过贯彻法则,而是通过铭写活过的经验。新的平等和自由,须由活过的经验来支撑才能广大。康德、席勒以来,我们一直期望:一个自由的人民,不再将艺术形式当作分开的宗教、政治和艺术来体验,在新的人类感性里,政治和艺术不再是两样不同的东西。艺术自我取消,进入集体生活的一种和同一种形式中。[5] 这种宗教、政治和艺术的三结合,也许正是张颂仁寄望于“礼”、“仪”和“教”合一的原因。这种三结合,在中国的20世纪里,也曾有过短暂和微妙的亮相,也一直被像林风眠这样的虔诚的艺术家们所热烈怀想。
因此猜想,张颂仁对于手中的艺术作品,也只抱托管的姿态,不是巴尔扎克笔下“邦斯舅舅”那样的揽文化于己任的忧世者,穿黑衣,匆匆于雨夜巴黎,怀揣作品,一脸凝重,私以为国族文化就系他于一线了。
八
那么,这“汉雅一百:偏好”展里,于右任、黄宾虹、方增先、张晓刚和王广义们的聚义,保存或托管了中国的20世纪的什么?
是不是可以说,这一作品群落,是关于中国的20世纪的第三种记忆、第三种历史,在官方提供的和我们心下意会的两种之外?在陵墓里,我们看到,帝王将相们总是抱着点什么往前走的。人民也总需要抱着一点什么,才能往前走。
但是,往前急急行军的人民,常会听不到、听不懂他们自己的声音,得不到自己的回声的鼓励,这时艺术作品就是他们的回声装置,是要来提醒他们,并向他们解释自己的声音和步伐,让他们被自己的声音伴奏着,继续向前走。“汉雅一百:偏好”保存的,正是20世纪中国人民的这种“声音”,值得展出的,正是这种来自那个世纪的回声?
这一百幅作品搭出的,是那个世纪的运动、情感、革命、记忆、纪念碑之外的更远处的“造型的风景”,是感块、知块和我们的成为。这就是“汉雅一百:偏好”?
九
在20世纪的中国,艺术经历了两种自我取消。延安或1949年后,艺术家自觉地成为人民的新的生活形式的建构者,去图解这个新的生活形式的建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他们的集体作品。而在“后八九”艺术运动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家重新学着西方艺术家的样,又试图去塑造日常生活的形式,用商品去美化资本主义式日常生活,来建构全球资本主义下中国当代的新生活形式。这两种方向,一个悲怆,一个谐谑,其实一直矛盾着;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是带着这一矛盾,走入21世纪的。到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仍在纠结:用艺术去拥抱,还是用革命去打碎?使革命成为纪念碑,还是使纪念碑成为革命?高氏兄弟和艾未未,F4和G8,就是这两个方向的当代变异的各自代表。
在“汉雅一百:偏好”的作品群中,这一中国20世纪艺术实践中的尖锐美学矛盾,惊天地暴露在我们面前,完爆了关于审美与政治的关系至今的全部艺术史叙述。由不得我们这样去问:这些,这一大片,算是症状,还是成就?
到20世纪,在冷战、“文革”和全球化的三个漩涡外,档案发了高烧,源头与终点被融化,混合到了一起。“没有这一高烧,没有这一档案的淫荡和失序,也就既不会有选派,也不会有移交。而选派就是移交。”[6] 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沸腾的资本主义桑拿场,面对来自过去的各异的源头的档案,我们不得不成为研究许诺、研究正在到来的东西的全新的历史学家。这些档案与其说与过去之发生、与当前之存在相关,更不如说与未来相关了。
这“汉雅一百:偏好”与我们的何种未来相关?
十
不论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总是先已掉在某种未来之中。
这相当于成为艺术家,去设计单人飞船,想独自去太空旅行。马雅可夫斯基式的革命先锋派的共产主义目标是:想干嘛,就干嘛,而且是一个人独自干,离开大家,独自出发,乘着玻璃飞船。艺术作品就是这样的一种能让我们星际迷航般回到今天的那一个个虚拟未来。它们是未来的草稿,也是未来的招贴。
艺术作品要将当前拖到未来之前。它在未来面前拷打当前。它要当前在未来面前自辩、脱罪。现在必须向未来负责!这曾是革命先锋派的姿态。正是用未来来审查当前,才使各种计划如此有意思。这之后,我们又回到老时间,与原来的现实同步。从艺术作品面前和美术馆里出来,我们感到自己在恍惚中是从未来回到了当前。
我们太过瘾于自己的计划,结束不了,一开始,就是不准备结束的。对于毛泽东而言,革命是一开始就注定不会完成的:大艺术家往往也都是这样说话的:这只是我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计划的百分之九十,都因为缺钱、时间和人力,才被搁置。好的,这也是好的,这种经验,这种态度,也是我们应该要和有的。[……]
艺术是个人或集体为多样的未来所作出的各种计划。最后是艺术来收容、保存那些失败的计划。我们在“汉雅一百:偏好”里能清晰地看到的,正是这种保存姿态。这是艺术作品的第二个历史使命:见证之外,去收留每一时代里的各种乌托邦计划。[……]
我们的“后八九”艺术运动虽然并没有收容革命时代的革命计划和艺术计划,却是一边挖苦它,一边又无能地去偷偷侵占它的历史遗产,占为已有,伪造其身份证件,倒卖和贩卖它。
艺术计划中的生命,被画面效果所决定,正如“文革”中的中国人民的生命,被当作了某种目标的手段来利用:我们都要学雷锋,为他的革命事业献身;生命是某种共同事业的工具。艺术是要用油画、绘画、摄影、录像和装置来记录革命或艺术计划中的生命的这种被生物权力支配的状态。艺术是要用文献去指称计划中的生命。这不是残酷,而艺术家是对生命政治操作的演示。
我们常说的“后文革”历史,就是这样的一种记忆与计划不可分,过去与未来杂交的“二”时代。这也是复活的时代:过去与未来,在当前,可以互换了。民国的、明朝的、汉朝的蓝图,随时会被我们激活,当成我们的未来招贴,或拼装材料。
在当代中国,有太多的计划,我们来不及关注每一个了。每一次,我们只能展示一种。而展示是消解的:在十五分钟里将某一张亮出,暂时将其余的都拉黑。艺术预设了这种种计划之间的平等。人类历史应该成为收藏这些失败或成功或被作者们放弃的计划的美术馆。“汉雅一百:偏好”所展示给我们的,远不止是我们在这诸多计划面前的无奈。它不给这些计划任何说法,只是收容它们。
中国20世纪的革命或乌托邦计划,其实有无数种、无数场。那些从未有机会实现的计划,其中的好一些,成了“汉雅一百:偏好”的收藏。可以说,这个艺术作品集合保全了一言难尽的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运动之外的很多风景。
十一
保全高于保存和保有。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作品需要保全者的收护,才能伟大。又说,整个文化和人民,才是作品的真正保全者,收藏家,是他们的代理。现代世界没给艺术留出位置,艺术作品找不到它的保全人了,所以,它们才需要收藏家。这一看法,与本雅明和阿甘本的看法重合:艺术作品收留和寄存于收藏家手中,等待重估。传统瓦解时,传统的精魂都残留到艺术作品中去了。是这些作品,将这一时代的人民的精神,寄托给了正在到来的未来的人民。
对海德格尔来说,还未找到保全者的作品,只是潜在作品。[7] 收藏的最高境界是,作品经收藏家托管之后,最终交由人民共同地来保全它。人民是能够在他们的共同生活里保全它所创造的东西的。而美术馆式的保存的最高境界,是希腊神庙、奥运会和音乐会形式,这都是要使“公共真理发生”,由作品打开世界,让人民进入其开阔地。“汉雅一百:偏好”是为未来的人民留着的一份沉重的遗产。它们最终的托付对象,只能是这一正在到来的人民。
保全,是人将世界体验为神圣、崇高,并将体验保存下来,交托给今后的人民。
在海德格尔看来,死,是人自祭于其世界那一刻,周围的物都亮了。这就像是,人一生是在准备一个关于他自己的展览,死时,那一个展览才开幕。人死时,是将其世界充分保全,交还给大地。
操心与保存,与开放者,也就是大地之间,达到透明——这才是保全。海德格尔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里推断出,斗争(polemos),时代之间、传统之间、文化之间、政治之间的斗争,才是真正的世界保全者。[8] 艺术是在这种“斗争”中被保全下的东西。
美术馆收藏的最高境界,只是保存。个人此在和共同体的生活,才能保全。对于个人而言,栖居,就是对于他们的个人生活场景的疼惜加保存。一开始,栖居者是被关怀者,先找到一块宁静的地方,脱离危险,安宁了,从那里开始,养足精神,然后开始去疼惜和保存周围的事物。栖居的任务,因此是使周围万物都能居于其本性之中。必死的人栖居,是他们在住的同时,养护着天地人神的四方域。[9] 人处于极大的危险时,就要去栖居;一旦开始栖居,人就为自己的死作准备。其一生的谋求,仿佛就为了使“自我献祭”做得尽量正确!周围的一切,都成为其礼器,各个细节都准备得周到,才走向结束,实际上是将失去控制,但仍希望筹划得它不出一点纰漏。
人自祭,也就是死时,身边的一切都将被保全,像艺术作品那样,被展出了。人能作出比保存更好的行动。
而共同体的集体生活,尤其是未来的人民的自由,才是今天的艺术作品的真正托付之处。
十二
保全、保存、持有、收留、拯救、引用,是“收藏”的各种姿态。
十三
艺术收藏押的是这样一个赌:谁手里的,将流传得更远?谁的,将更有代表性?谁的,更提纲挈领?谁的,更石破天惊?……收藏家的幸福,在于尽早预感到:我收藏的作品里的被人民集体体验过的感块和知块,将最终被保存得更久!
所有被保存的东西里,用艺术保存下来的,将流传得最远,会超过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器物的寿命,会超过礼器和仪式的流传,且更不失真。希望这样的寄想,能给张颂仁带去安慰。
十四
“只要画布不烂,这年轻人就将笑到永远。这个女人的皮肤下涌动着血液,风摇动着树枝,一群人准备离开。在一部小说或电影里,年轻人的笑将停下来,但当我们翻到那一页,或观看到那一瞬间,他就又开始笑了。”[10]
[1] Gilles Deleuze,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Editions de Minuit, 1991/2005, p.154.
[2] Walter Benjamin,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参见:http://www.sfu.ca/~andrewf/CONCEPT2.html.
[3] 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and Other Writings on Med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04.
[4] Ibid., p. 21.
[5] Jacques Ranciere, Aisthesis: Scenes from the Aesthetic Regime of Art, trans. Zakir Paul, Verso Books, London, 2013, p.177.
[6] Jacques Derrida, “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 Diacritics, Vol. 25, No. 2, Summer,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52.
[7]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 Albert Hofstadter, Harper & Row Press, 1971, pp. 66-67.
[8] Martin Heidegger,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trans. Ralph Manhei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61-62.
[9]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pp. 150-151.
[10] Gilles Deleuze,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p. 154.
“汉雅一百:偏好”汉雅三十年庆之“三个艺术世界”论坛发言稿
一
画在拉斯科岩洞石壁上的马儿,已向我们证明,艺术作品能被保存到永远,超出历史谱系,久过美术馆、博物馆、纸、布、皮、墨、色本身的物质寿命。
艺术本身就是保存行为。艺术本身,而不是人的算计和操持,才是保存的最好方式。最好的艺术收藏,也只是使收藏行为本身成为艺术行动,任作品里的艺术,自己去保存自己到永远。最高等级的收藏行为,是自己成为一个艺术行动,不用人为支持地让自己保存到永远。
收藏行为的最根本姿态,是这种:让,任……
二
哲学家吉尔·德勒兹说,艺术是要去保存作品里的感块(affect)和知块(percept)了,而它也是这世界上唯一能自我保存的东西。它保存,并在它自身之上自我保存。这句话强调:艺术是“唯一能自我保存”下去的东西,连收藏这一手段,也不算添助,还不够,自己保存不了自己;收藏行为也必须先成为艺术行动,才能让自己不依赖于任何手段,像艺术那样地去永远地自我保存。
看来,并不需要我们拿出专门的套路、格式和技术,去保存艺术,而是反过来,先去成全艺术,顺着它的自我保存,去保存它;它是:帮那能够自我保存的艺术去自我保存。收藏这一行为的唯一目标,是成为艺术那样的行为,化身于艺术这一最大的保存行为之中。收藏,然后保存,然后流传,到了最后,就只有艺术,没有收藏和收藏者,没有作者,也不依赖于画框和画布了:“瞧,这个姿势,这年轻姑娘在那里已摆了五千年的姿势了,已不再依赖于谁画出它,谁来看了。是艺术将这个姑娘的这个姿势,保存到了永远。”
保存艺术作品,是为了保存作品内的另外的东西(“作品”只是一个框)。这另外的东西是什么?它是那能够自我保存的东西。德勒兹说:“[……]自我保存下来的东西,物或艺术作品,是感性的一块,保存下来的,是感块和知块的合成。”[1] 用艺术去保存,是从我们的感性、知觉和观点中抽离出感块和知块,后者才能够永远自我保存下去,能流传的,只是这些块块。
做艺术是要保存,做收藏是要通过先成为艺术,艺术地去保存,然后艺术地去保存那自己就会去保存的东西,留下来,真正能流传的,是那些感块和知块,后者并不依赖于我们的美术馆和博物馆,甚至其寿命都将远超出我们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经济制度,像在岩洞石壁上的原始绘画上的那些块块一样,一直坚挺到今天。
最终,以长焦距看,做收藏和做艺术,是在做同一回事:保存,更大意义、程度上的保存(下文我们将讨论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生存论意义上的“保存”)。做艺术收藏,是要比共同体、社会和时代所要求的还更长久地去保存,是要比共同体、社会和时代更长久、超过它们本身的寿命地去保存那些留下的感块和知块……
那也就是说,最高等级的收藏,是艺术,是保存,是要比我们时代的美术馆更可靠地使我们时代的收藏成为艺术,并利用这种艺术的自我保存,来保存我们的所保存,使之流传,挺持、残存、挥之不去……
三
在《历史哲学论纲》中,瓦尔特·本雅明向我们指出,过去的真正图像(das wahre Bild)(过去作为一片片图像?来自过去的一片片图像?过去本身作为一片片图像?),正飞快地飘离我们。而过去只有作为图像,才为我们所把握。它总在可被我们认识的那一刻弹出,旋即湮没……过去的图像一旦不能成为当前的关怀,被我们认出,就将永远不可追回。图像并不是过去在当前打下的烙印,或者是当前在过去投下的阴影;图像是那已经存在过的东西,在某一闪忽中,与当前结合了,是过去与当前形成的一个星丛或聚合(constellation)。[2] 在图像中,过去和当前在某一瞬间里连接、聚合,在其中,当前才能够认出过去的意义,过去也在当前中寻找到了它的意义和完成。图像是某个过去与当前的联合。
由此看,一切过去的艺术作品,可以说都是当代艺术作品;展览的使命,是使过去的一切艺术作品在今天仍然成为艺术作品,使古画、近画和今画重合。收藏来自过去的图像,是将它们汇合在当前的时间刻度上。站在当代,或以当代艺术的态度,去接受来自过去的图像,这就是收藏了。
收藏是尊重图像自身的方式,将过去引用到当前。通过引用,过去的许多代人,才与当代人之间有了神秘的相遇。是引用牵了线。本雅明指出,引用不在于保留,而在于毁坏:引用通过叫出其名字,而将字和画叫到我们眼前,毁灭性地将字和画从它的上下文里攥出来,但正因此,也将它唤回根源;引用在拯救的同时,也加以惩罚。(《历史哲学论题》)在《什么是史诗剧》里(《选集》,第151页),他说,引用是对上下文的打断。破坏了上下文,引用才能成功。引用是救赎,是要将字和画,从过去的锁链中解放出来;引用而不加引号,才是真正的救赎:引用一成功,弥赛亚就降临。而收藏是不成功的引用。它也是暴力的引用。
今天要借助收藏行为,是因为,我们越来越不善于引用了。本雅明说:“就如我们之前的好几代人那样,我们被赋予越来越弱的弥赛亚力量。”这样说,不是悲观。他接着说,病弱、责难、必然性、迫害和绝望,反而会使弥赛亚早日降临。我们的收藏行为越来越弱,越来越不自信,但这反而会促使我们引用得更迫切,被救赎得更快些。收藏是迫不及待和不顾一切的引用。
引用或收藏(作者和艺术家其实都是很好的引用者或收藏家),活像埋伏在路边的强盗,用刀逼着路人,要抢走他们的确信。当代人没了确信,才去抢劫过去的作者的确信?收藏,是在猎取前代人的“确信”?在本雅明看来,过去只是被割掉了上下文,破坏了,才放到我眼前的。过去只有被一种异化的力量(比如说我们当前的收藏)攫住,才可见。那一过去,只有在这样的被异化、被毁灭的瞬间,才露脸。就像在大的危险中,某种记忆才惊艳地闪现。直白地说,过去的字和画,也必须在被当代人抢劫,也就是说被引用和收藏之后,才露脸。到这里,本雅明露出了他对收藏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收藏了,被粗暴地引用,被不法地征用和没收之后,历史作品才有机会露脸,才会得到有利的评价。
本雅明眼中的收藏家,是一个将作品拖出去,毁除它的上下文关联,将其紧紧搂在怀里的人。他们引用,由此而夺走作品或商品的使用价值,或社会-伦理意义。作品的正宗与否,是由作品和商品被这样引用之后产生的异化的大小来衡量:越正宗,它被异化得就越严重。越收藏,就越异化。我们评价一个被收藏的作品,是看它与我们今天、当前的历史境遇的相异程度,来定其价值和意义。越与我们本时代相异,被收藏作品就越伟大吗?拿出旧东西,本身也就是在排挤、架空新东西?
这么说,收藏家与革命家的角色相辅相成。对于革命家,新东西的出现,必须以毁灭旧东西为前提。所以,在传统社会的稳定秩序里,引用和收藏,是不大可能的。只有在与传统的决裂期,和毁坏后的复兴期,收藏和引用才又兴盛起来。在我们今天这样新和旧、全球和本地脱节的离异时代里,收藏也极度活跃了。收藏促进了各种各样的“换手”,这一道道的换手,更促进了收藏?对于作品,这是一个颠沛游离的时代,对于收藏者,却是一个如鱼得水和游刃有余的时代。下面我们将看到,张颂仁的艺术收藏,却发生在三个时代的汇合、平行处。
四
对于艺术作品收藏家,中国大陆的20世纪,是一个乾坤大挪移的时地。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冷战景观式分离与合并,将人类的各种历史时空挤进同一个世纪中。
而身处中国香港的张颂仁,像蝴蝶一样,采集着其中的花粉。2014年1月18日开展的“汉雅一百:偏好”大展,就是他自己的“中国20世纪”!正如策展人高世名所说,这个展览收容了“中国传统艺术世界、中国社会主义艺术世界和全球资本主义艺术世界三种艺术生产和艺术机制”,汇合了中国古典艺术、民国艺术、革命时代艺术和后八九艺术运动。刘大鸿的《祭坛》,方增先的《唤起工农千百万》和陆俨少的《山水》,被放到了同一个时空里,同一个展览装置内,像一坛新酿的百年陈的黄酒:近、现、当代被“吊”到了同一种20世纪的“味”中。
五
要成为艺术作品,一个制品须被切断其文化传承,献祭给一个展览空间。为了艺术而艺术,艺术家须杜绝引用这个时代。现代艺术切断了我们与过去的联系;过去作为废墟越积越多,而我们越来越掉进当前的深渊里。只有拯救,才能打捞这高堆的废墟一样的过去或传统,但在弥赛亚到来前,这又是无望的。文化,我们不要;过去,也只剩其文化价值了。我们要用艺术另找和另搞。像在谷堆前饿昏过去的天使,在等待救赎的过程中,我们没有什么依仗,只有手里捧着的艺术作品这一道具了。一切都在从我们指间滑去,留在手上的唯有艺术这一保存手段了。
我们无法保存整个过去,收藏是我们不顾历史和文化脉络地去引用的姿态。引用或收藏,本身是一种毁灭式暴力,是要切断艺术品与过去、传统的全部联系,不顾一切地将遗物挪用到当前。过去和传统只是堆积的垃圾,作品无法在这样传述的废墟堆里重新得到权威的支撑。这时,只有收藏家,才会站出来干预,成为艺术品之意义和价值的庇护人。有如此多的艺术品沦为无处安放的碎片,收藏家就担起了一种假托的权威下的庇护责任,使艺术作品在无历史、无传统或传统和历史停滞或搁浅的时代里,有一个人工支撑的档案意义的来源。
这是收藏的要害:在并不清楚地知道那最终被保存到、流传到永久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之前,收藏家就必须出手。这一冒险举动,短期的,称作艺术,长期的,称作收藏。收藏家必须站到比艺术家、艺术史、文明史更高远的立场上,去作出保存的姿态。
在〈爱德华·富克斯:收藏家和历史学家〉(Eduard Fuchs: Collector and Historian,1937)一文中,本雅明指出,富克斯的最大的收藏功绩,或许就在于他“披荆斩棘,将艺术史从我们对大师名字的拜物中解放出来”。伟大收藏家必须“观察那些人们根本看不起、离经叛道的事物,那正是他(或她)的真正长处”。他们必须抱有真正的宽容,和长距离的眼光,执行西西弗斯式的苦劳:通过占有,来脱去物的商品特性。可他们这样辛苦,也只为了赋予物以鉴赏家眼里的价值,并不能给物重新带去使用价值。可他们梦想的,恰恰是进到远古或失去的世界,还想进到一个更好的世界里。他们想要这样一个世界:人们并没有被赋予比日常世界所需更多的东西,在其中,物都摆脱了必须有用这一苦役,所有物品都找到了自己的独一无二的角色。[3]
这种收集的姿态,正是哲学家乔吉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说的“亵渎”:通过收藏后重新展出,将(艺术)商品从流通的苦役中解放出来,放入共同体的全新的集体使用之中。究底看,收藏家要解放商品于苦役,解放人于其消费。对市场而言,收藏艺术作品,是使像陀螺一样陷于流通和交易的艺术商品,重新成为艺术品,通过新的展出,以新的形象,亮相公众之前。收藏家在当代还有另外一个重大的任务,那就是:不要使艺术作品泛滥,通过收藏,使当今的艺术作品能以正常速度流通,这类似于中央银行的回收流动性。
我们引用,是为了利用作品的权威。但我们的引用,又会毁坏被引用的东西的上下文,因而破坏了其出处、身份的权威性。在我们时代,艺术作品失去了它的通过权属于某一传统、某一地点、某一源头而携带的权威性。作品的正宗不正宗,如今已只成了复制得好不好的问题。原作不原作,正宗不正宗,是由市场和媒体来担保了。“做旧”的技术总有一天会压倒专家鉴定的权威。这种百分百的复制,这种所谓的山寨,表面上看是对收藏的毁灭性打击,但在本雅明看来,也是好事:一、技术复制比原作的手工制作更可靠;二、技术复制使原作能存活于更多的地方,其幸存概率大增。典型的例子就是摄影:更好的复制,才能达到更好的收藏。[4]
从此,艺术作品再也不能依靠传统和权威来获得意义,而只能从收藏者那里去寻求庇护和保值。艺术史也成了一道不合缝的篱笆。文化成了垃圾焚烧场。一切艺术作品的命运,都须在收藏者手里了断。全部的艺术史,将断送在他们手里。劫后余生的艺术品,也全要他们的收留,来苦撑出自己的意义。收藏家是艺术的未来法人。我们至今还远远没有了解美术馆对于艺术和艺术作品的全部意义,在此之前,我们请收藏家先代理着美术馆的未来功能。
六
这样的局面,并不是哲学的断想,而是真真切切地发生到了中国的20世纪!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张颂仁幸运地撞上了它!我们不难发现,他手里拿着它的总谱。不由得要妒忌他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经历。他像激动的孩子那样,抖着手告诉我们:我看见了,我看清楚了,有好多样,我取舍不了,都留下来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拿它们如何是好,那就先存而勿论吧!
张颂仁的汉雅轩,说起来,就是一个中国大陆20世纪馆。因为我们的民族历史叙述在20世纪,被世界历史事件挤爆了,或者说,我们突然有了三种以上的平行历史,或者说,我们把历史当宣传,伪造历史上了瘾,副本太多,找不回源初了。因此,这个20世纪馆就重要了。
这么说,是因为,艺术作品比起其他档案,更好地见证了20世纪的中国。电影导演戈达尔就认为,拍20世纪的电影史,能拍得比写出的20世纪的历史更真,因为,电影见证了它。拍这种见证,比直接去拍历史,会更真实。戈达尔认为,20世纪的电影史,是电影的沉沦史,而这一史,比20世纪历史,更能说明人类在这一世纪中的遭遇。他这强调的是艺术作品的“见证”能力。爱森斯坦也指出,电影里的十月革命比现实里的、历史叙述中的十月革命,要更真实。
那么,汉雅轩给我们保留着怎样的一个中国20世纪呢?
七
“汉雅轩”成立三十周年了。张颂仁的艺术收藏家位置,仍待重估。他对自己的收藏家身份,也继续三心二意。对他所收藏的主要作品的跨年,也就是中国的20世纪,他至今仍抱暧昧态度。他好淡定。
在美国受过精英教育,旁观了中国的革命和后革命,他至今仍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基督教和汉族礼教三者之间走着跳棋,或者说,举棋而不定着。不过,可以想见,他理解西方越多,似乎越认准了这一点:做中国人这件事,必须整顿了!他要“复辟”的,是中国人原来行事、设论和立命的简单、沉着和管用。
张颂仁理解的“艺术”,在我看来,是更宽广的一种象征活动,是礼器加仪式。他想要恢复的,是礼器与生活、艺术与共同体之间的更本真的关系。他等待的是将要到来的人民,而不是我们原来有过的生活,或我们过去所沉浸的生活之艺术。艺术作品必须抹煞自己,成为生活必需品,那个人民才会到来。他的这种态度,译成康德、席勒或马拉美后的美学语言,可以表达成:艺术必须成为“生活的艺术”,帮我们过渡到共同体新的感性域,超越有文化的阶级的精致,与没文化的阶级的朴素天性之间的对立。艺术作品通向个人与共同体的新的生活,不光是民族的自身成就,更成为对新人类的许诺。希望这次的“汉雅一百:偏好”展能使作为收藏家的张颂仁更坚信,艺术作品不光能保存一个世纪的迭宕的频谱轨迹,更是激励人民的生活之艺术的全新“礼器”。
艺术比政治更擅长推动新的人类共同体的建立,不是通过贯彻法则,而是通过铭写活过的经验。新的平等和自由,须由活过的经验来支撑才能广大。康德、席勒以来,我们一直期望:一个自由的人民,不再将艺术形式当作分开的宗教、政治和艺术来体验,在新的人类感性里,政治和艺术不再是两样不同的东西。艺术自我取消,进入集体生活的一种和同一种形式中。[5] 这种宗教、政治和艺术的三结合,也许正是张颂仁寄望于“礼”、“仪”和“教”合一的原因。这种三结合,在中国的20世纪里,也曾有过短暂和微妙的亮相,也一直被像林风眠这样的虔诚的艺术家们所热烈怀想。
因此猜想,张颂仁对于手中的艺术作品,也只抱托管的姿态,不是巴尔扎克笔下“邦斯舅舅”那样的揽文化于己任的忧世者,穿黑衣,匆匆于雨夜巴黎,怀揣作品,一脸凝重,私以为国族文化就系他于一线了。
八
那么,这“汉雅一百:偏好”展里,于右任、黄宾虹、方增先、张晓刚和王广义们的聚义,保存或托管了中国的20世纪的什么?
是不是可以说,这一作品群落,是关于中国的20世纪的第三种记忆、第三种历史,在官方提供的和我们心下意会的两种之外?在陵墓里,我们看到,帝王将相们总是抱着点什么往前走的。人民也总需要抱着一点什么,才能往前走。
但是,往前急急行军的人民,常会听不到、听不懂他们自己的声音,得不到自己的回声的鼓励,这时艺术作品就是他们的回声装置,是要来提醒他们,并向他们解释自己的声音和步伐,让他们被自己的声音伴奏着,继续向前走。“汉雅一百:偏好”保存的,正是20世纪中国人民的这种“声音”,值得展出的,正是这种来自那个世纪的回声?
这一百幅作品搭出的,是那个世纪的运动、情感、革命、记忆、纪念碑之外的更远处的“造型的风景”,是感块、知块和我们的成为。这就是“汉雅一百:偏好”?
九
在20世纪的中国,艺术经历了两种自我取消。延安或1949年后,艺术家自觉地成为人民的新的生活形式的建构者,去图解这个新的生活形式的建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他们的集体作品。而在“后八九”艺术运动之后,中国当代艺术家重新学着西方艺术家的样,又试图去塑造日常生活的形式,用商品去美化资本主义式日常生活,来建构全球资本主义下中国当代的新生活形式。这两种方向,一个悲怆,一个谐谑,其实一直矛盾着;中国的当代艺术,也是带着这一矛盾,走入21世纪的。到今天,中国的当代艺术家们仍在纠结:用艺术去拥抱,还是用革命去打碎?使革命成为纪念碑,还是使纪念碑成为革命?高氏兄弟和艾未未,F4和G8,就是这两个方向的当代变异的各自代表。
在“汉雅一百:偏好”的作品群中,这一中国20世纪艺术实践中的尖锐美学矛盾,惊天地暴露在我们面前,完爆了关于审美与政治的关系至今的全部艺术史叙述。由不得我们这样去问:这些,这一大片,算是症状,还是成就?
到20世纪,在冷战、“文革”和全球化的三个漩涡外,档案发了高烧,源头与终点被融化,混合到了一起。“没有这一高烧,没有这一档案的淫荡和失序,也就既不会有选派,也不会有移交。而选派就是移交。”[6] 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沸腾的资本主义桑拿场,面对来自过去的各异的源头的档案,我们不得不成为研究许诺、研究正在到来的东西的全新的历史学家。这些档案与其说与过去之发生、与当前之存在相关,更不如说与未来相关了。
这“汉雅一百:偏好”与我们的何种未来相关?
十
不论有没有意识到,我们总是先已掉在某种未来之中。
这相当于成为艺术家,去设计单人飞船,想独自去太空旅行。马雅可夫斯基式的革命先锋派的共产主义目标是:想干嘛,就干嘛,而且是一个人独自干,离开大家,独自出发,乘着玻璃飞船。艺术作品就是这样的一种能让我们星际迷航般回到今天的那一个个虚拟未来。它们是未来的草稿,也是未来的招贴。
艺术作品要将当前拖到未来之前。它在未来面前拷打当前。它要当前在未来面前自辩、脱罪。现在必须向未来负责!这曾是革命先锋派的姿态。正是用未来来审查当前,才使各种计划如此有意思。这之后,我们又回到老时间,与原来的现实同步。从艺术作品面前和美术馆里出来,我们感到自己在恍惚中是从未来回到了当前。
我们太过瘾于自己的计划,结束不了,一开始,就是不准备结束的。对于毛泽东而言,革命是一开始就注定不会完成的:大艺术家往往也都是这样说话的:这只是我工作中很小的一部分,计划的百分之九十,都因为缺钱、时间和人力,才被搁置。好的,这也是好的,这种经验,这种态度,也是我们应该要和有的。[……]
艺术是个人或集体为多样的未来所作出的各种计划。最后是艺术来收容、保存那些失败的计划。我们在“汉雅一百:偏好”里能清晰地看到的,正是这种保存姿态。这是艺术作品的第二个历史使命:见证之外,去收留每一时代里的各种乌托邦计划。[……]
我们的“后八九”艺术运动虽然并没有收容革命时代的革命计划和艺术计划,却是一边挖苦它,一边又无能地去偷偷侵占它的历史遗产,占为已有,伪造其身份证件,倒卖和贩卖它。
艺术计划中的生命,被画面效果所决定,正如“文革”中的中国人民的生命,被当作了某种目标的手段来利用:我们都要学雷锋,为他的革命事业献身;生命是某种共同事业的工具。艺术是要用油画、绘画、摄影、录像和装置来记录革命或艺术计划中的生命的这种被生物权力支配的状态。艺术是要用文献去指称计划中的生命。这不是残酷,而艺术家是对生命政治操作的演示。
我们常说的“后文革”历史,就是这样的一种记忆与计划不可分,过去与未来杂交的“二”时代。这也是复活的时代:过去与未来,在当前,可以互换了。民国的、明朝的、汉朝的蓝图,随时会被我们激活,当成我们的未来招贴,或拼装材料。
在当代中国,有太多的计划,我们来不及关注每一个了。每一次,我们只能展示一种。而展示是消解的:在十五分钟里将某一张亮出,暂时将其余的都拉黑。艺术预设了这种种计划之间的平等。人类历史应该成为收藏这些失败或成功或被作者们放弃的计划的美术馆。“汉雅一百:偏好”所展示给我们的,远不止是我们在这诸多计划面前的无奈。它不给这些计划任何说法,只是收容它们。
中国20世纪的革命或乌托邦计划,其实有无数种、无数场。那些从未有机会实现的计划,其中的好一些,成了“汉雅一百:偏好”的收藏。可以说,这个艺术作品集合保全了一言难尽的中国20世纪的历史运动之外的很多风景。
十一
保全高于保存和保有。哲学家海德格尔说,作品需要保全者的收护,才能伟大。又说,整个文化和人民,才是作品的真正保全者,收藏家,是他们的代理。现代世界没给艺术留出位置,艺术作品找不到它的保全人了,所以,它们才需要收藏家。这一看法,与本雅明和阿甘本的看法重合:艺术作品收留和寄存于收藏家手中,等待重估。传统瓦解时,传统的精魂都残留到艺术作品中去了。是这些作品,将这一时代的人民的精神,寄托给了正在到来的未来的人民。
对海德格尔来说,还未找到保全者的作品,只是潜在作品。[7] 收藏的最高境界是,作品经收藏家托管之后,最终交由人民共同地来保全它。人民是能够在他们的共同生活里保全它所创造的东西的。而美术馆式的保存的最高境界,是希腊神庙、奥运会和音乐会形式,这都是要使“公共真理发生”,由作品打开世界,让人民进入其开阔地。“汉雅一百:偏好”是为未来的人民留着的一份沉重的遗产。它们最终的托付对象,只能是这一正在到来的人民。
保全,是人将世界体验为神圣、崇高,并将体验保存下来,交托给今后的人民。
在海德格尔看来,死,是人自祭于其世界那一刻,周围的物都亮了。这就像是,人一生是在准备一个关于他自己的展览,死时,那一个展览才开幕。人死时,是将其世界充分保全,交还给大地。
操心与保存,与开放者,也就是大地之间,达到透明——这才是保全。海德格尔从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那里推断出,斗争(polemos),时代之间、传统之间、文化之间、政治之间的斗争,才是真正的世界保全者。[8] 艺术是在这种“斗争”中被保全下的东西。
美术馆收藏的最高境界,只是保存。个人此在和共同体的生活,才能保全。对于个人而言,栖居,就是对于他们的个人生活场景的疼惜加保存。一开始,栖居者是被关怀者,先找到一块宁静的地方,脱离危险,安宁了,从那里开始,养足精神,然后开始去疼惜和保存周围的事物。栖居的任务,因此是使周围万物都能居于其本性之中。必死的人栖居,是他们在住的同时,养护着天地人神的四方域。[9] 人处于极大的危险时,就要去栖居;一旦开始栖居,人就为自己的死作准备。其一生的谋求,仿佛就为了使“自我献祭”做得尽量正确!周围的一切,都成为其礼器,各个细节都准备得周到,才走向结束,实际上是将失去控制,但仍希望筹划得它不出一点纰漏。
人自祭,也就是死时,身边的一切都将被保全,像艺术作品那样,被展出了。人能作出比保存更好的行动。
而共同体的集体生活,尤其是未来的人民的自由,才是今天的艺术作品的真正托付之处。
十二
保全、保存、持有、收留、拯救、引用,是“收藏”的各种姿态。
十三
艺术收藏押的是这样一个赌:谁手里的,将流传得更远?谁的,将更有代表性?谁的,更提纲挈领?谁的,更石破天惊?……收藏家的幸福,在于尽早预感到:我收藏的作品里的被人民集体体验过的感块和知块,将最终被保存得更久!
所有被保存的东西里,用艺术保存下来的,将流传得最远,会超过社会-政治制度和文化器物的寿命,会超过礼器和仪式的流传,且更不失真。希望这样的寄想,能给张颂仁带去安慰。
十四
“只要画布不烂,这年轻人就将笑到永远。这个女人的皮肤下涌动着血液,风摇动着树枝,一群人准备离开。在一部小说或电影里,年轻人的笑将停下来,但当我们翻到那一页,或观看到那一瞬间,他就又开始笑了。”[10]
[1] Gilles Deleuze,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Editions de Minuit, 1991/2005, p.154.
[2] Walter Benjamin, Theses 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参见:http://www.sfu.ca/~andrewf/CONCEPT2.html.
[3] Walter Benjamin, The Work of Art in the Age of Its Technological Reproducibility, and Other Writings on Medi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104.
[4] Ibid., p. 21.
[5] Jacques Ranciere, Aisthesis: Scenes from the Aesthetic Regime of Art, trans. Zakir Paul, Verso Books, London, 2013, p.177.
[6] Jacques Derrida, “Archive Fever: A Freudian Impression,” Diacritics, Vol. 25, No. 2, Summer,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5, p.52.
[7]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 Albert Hofstadter, Harper & Row Press, 1971, pp. 66-67.
[8] Martin Heidegger, An introduction to metaphysics, trans. Ralph Manheim,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61-62.
[9] Martin Heidegger,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pp. 150-151.
[10] Gilles Deleuze, Qu'est-ce que la philosophie? p. 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