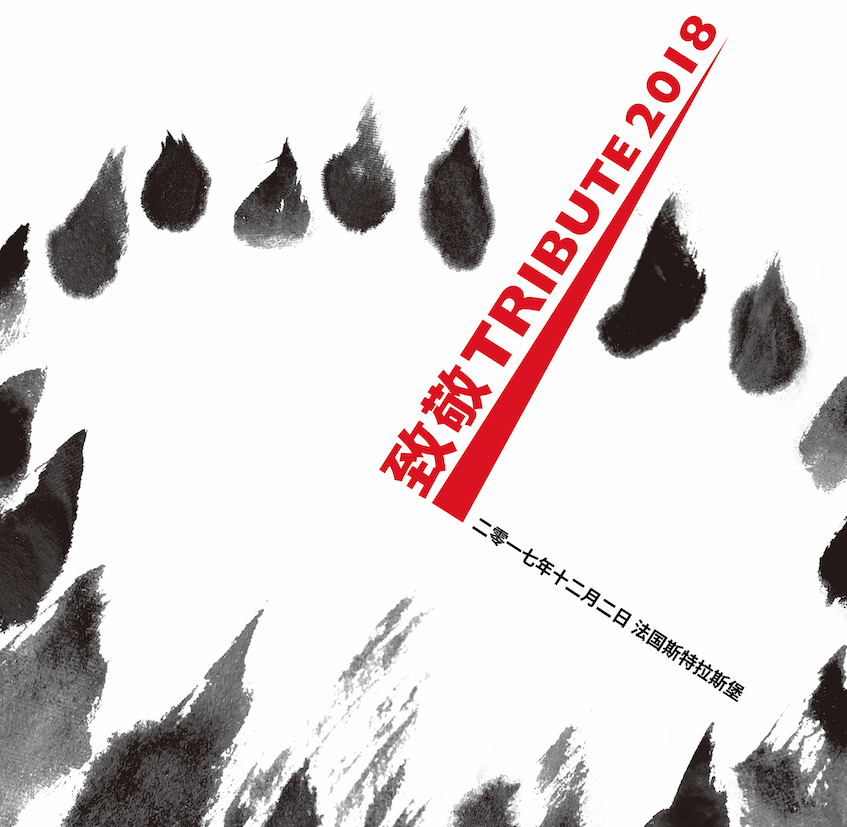2017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于2017年12月2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主办的“世纪:一个提案”论坛上的讲演
1954年或1956年,应该说是冷战第一阶段在50年代中期左右形成的结晶。我想谈一谈其中发生的巨大分裂及这些分裂所经历的突变。我从苏伊士运河和苏伊士运河危机谈起,这是全球贸易中的关键节点。因为苏伊士运河危机既代表了前殖民地或仍处于被殖民状态的世界要求自决的主张,也意味着权力从大英帝国转移到了宣称拥有全球霸权的新霸权——美国。
遏制论是全球霸权主张的一部分。对共产主义的遏制引发了十年来及其后发生的诸多危机,并且也酝酿了许多紧随而来的危机。台海危机、越南战争,以及我们还能说出名字的许多地方,那里的民主进程经常被秘密机构推翻。当然,在冷战的超声图像中,艺术和文化自然也扮演了一个新的角色。为了引起注意,我想读一段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说过的话。他是一名外交官,曾在莫斯科为美国效力,1955年他在国际现代艺术博物馆国际理事会上发表了讲话。凯南也是遏制论的核心制定者之一。而在美国和西方所谓的文化冷战中,他也参与发起了全球性的运动。凯南是这么说的:
当然,实际上,我们此时有最大、最迫切的需要去纠正外界对我们的一些印象。这些印象正在开始对我们的国际地位产生重大影响。我认为,我们第一次意识到,这些他国一定程度上占据主导的负面看法可以达到何种可怕的程度。然而,这些负面情绪在多大程度上与文化而非政治条件有关,我们许多人对此仍旧无知无觉。
所以在此,你可以清楚地看到,为什么在越来越关乎软实力方式的冷战中,权力被列为一种和平武器。
同时,为什么是艺术?那些在我们耳熟能详的20世纪30年代的伟大战争的感召下努力奋斗的人,那些曾经努力一方面与前卫重新建立联系,另一方面也为自己创造新的根据地的人,总是在这场新的文化冷战中黯然失色,或者被一种过于简化的议程所利用。他们对此不得以一种近乎颠覆与反颠覆的语言做出反应。我想把20世纪50年代作为充斥着虚假普遍性的十年来讨论,在我看来,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的否定普遍历史概念可能是一个克服这种虚假性的方法。我的观点是,在1950年代,普遍性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被认为是否定的。当然,宣扬普遍历史和普遍性的论调自那以后已偃旗息鼓。但近年来,普遍性概念不仅经历了在历史书写中的光荣回归,还自然经历了“人类纪”这类概念的提出。
首先,普遍历史到底出了什么问题?问题出在,说出普遍性之语言的人总是口是心非。问题出在,法国之类的国家所倡导的关于人之权利的普遍论述与殖民压迫的现实严重不符。法国不仅是一个共和国,而且如我们所知,还是一个帝国。1954年,法国输掉了战役,继而在当时被称作印度支那的法属殖民地败退,此后阿尔及利亚战争爆发了。但回到口是心非这个问题上来,启蒙事业的论述与殖民意识形态,正是通过这种变戏法般狡黠的方式被确立了:在说着自由和普遍性的语言时,不自由和压迫的现实在某种程度上变得不可说、不可见、被排除。当你会因被压迫者的回归而困扰,这就是普遍性。口是心非是官方话语与压迫现实之间的分界线,这条线贯穿在那些话语当中,这点对于理解宰制系统如何被构造出来至关重要。
在1950年代中叶,这条分界线以三种形式出现,对应着三个突变。第一个突变发生在军事层面,以氢弹的出现为标志。这是一种普遍性,因为摧毁性的力量已经是全球性的了。1954年美国在比基尼环礁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氢弹试爆。毁灭的可能,甚至人类灭绝在人类自己手上的普遍威胁,如今已迫在眉睫。蘑菇云的形象也是文明的绝对极限的形象,因此,氢弹仅以其普遍毁灭的能力,体现了否定的普遍历史。这条界线曾一度是军事前沿,在武器技术的协助下,它允许某些统治的组织结构及其不对称性的形成。假想一下,被发明出来的火药或者机枪现在已包裹着地表,如同人造卫星搭载着一枚核弹绕着地球转。我要插入一句阿多诺的引言,阿多诺说“普遍历史必须被解释并否认”,而他同样说了“不存在从野蛮走向人道主义的普遍历史,尽管毋庸置疑有一段从弹弓走向百万吨级炸弹的历史”。
这条分界线的第二个突变是,这种威胁是如何在冷战期和超级大国间的“恐怖均衡”中被牵制住的。“铁幕”一直是这种对立的象征,但是这种对立同样使得在普遍话语中表现出来的危机成为殖民现代性的宏大叙事,无论是黑格尔的版本,还是其马克思主义的取代或彻底颠覆版本。必须指出的是,这两者在本质上仍然在行使教化(civilizing)的使命,并且和现代官僚国家机器的兴起密切相关。而在1950年代人类灭绝的威胁和世界大战的暴力之背景下,这种叙事猛增到了令人恐惧的程度。在西方,这种叙事的拥护者们试图重新获得对普遍性的掌控,回复将他者放入框架的能力,不惜以应允他者自主决定与自行代表的权利为代价。当然,在现实中,这一权利仍然需要用鲜血来换取。
这样一种普遍性之中,人权被营救为破产的人道主义,对其把握得最为精准的,或许是1950年代的展览“人类一家”(The Family of Man)所体现的政治。此著名展览于1955年开幕,在接下来的七年里穿越了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向数以百万计的人传递教义,从危地马拉城到日本,从莫斯科到柏林。如果我有更多的时间,我希望能向你们展示一张在那次展览中展出的著名的核试验照片,以及它被从展览上撤下的时刻。在讨论这个展览所体现的普遍性的虚假(至少在批评者眼中如此)时,人们还谈及了毕加索的《格尔尼卡》,以及这幅画不知为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其特殊性,即一幅反对暴力、为恐怖活动的广大牺牲者代言的图像。
分界线的第三个突变与铁幕所体现的殖民现代性的精神分裂危机完全背道而驰。而且这一次突变设起了一道与铁幕对立的“种族幕墙”(color curtain)。这是美国小说家理查德·赖特(Richard Wright)对杜波伊斯(W. E. B. Du Bois)在最初用于描述1900年以来的种族分裂的世界时使用的“肤色界线”一词的改述,从而将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历史映射到冷战上。在我看来,这条分界线必须被视为1950年代中期的典范性事件。同样在消极普遍主义的意义上,关于1955年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万隆会议,理查德·赖特为自己对其所写的报道命名为“种族幕墙”。会议以对全球共同体的呼吁开场,但呼吁的基础首先是一种共同的灾难感:即对殖民征服和启蒙理性破产的恐惧。
我在这里插一句:在我看来,在50年代中期,我们所拥有的状况是由这两条分界线之间的关系决定的——铁幕相对于种族幕墙;也是被这样一个问题决定的,当时似乎只有一种消极的普遍主义能够规定一个全球的未来,这种消极的普遍主义基于一种共同的灾难感,在未来的全球政治,以及生态灾难和气候变化的迹象中,这种灾难感再次现出端倪。
最后,这条分界的最后一个突变也许正在以完全消失的危险在威胁着我们。20世纪50年代同样也被计算通信理论、控制论和系统科学的兴起所定义。在这段简短演讲的最后,我想指出,在数字时代到来之际,在信息理论的影响下,人与机器的整合产生了量子飞跃。同样因为我认为现在明确无疑的是,数字技术和全球联系并不能代替主动的意识形态事业;仅仅是全球联通并不能产生一个普遍的公民社会。无处不在的媒体无法救赎现代性的难题,所以50年代中期也同样被资本主义所定义,而这种资本主义借助于控制论来创造和平时期的战争——冷战。
20世纪50年代的两本重要著作——我也可以选择别的,但这两本在我看来更为切题,它们指向当下的自动化发展和人机一体化——罗斯·阿什比(W. Ross Ashby)的《脑之设计》(Design for a Brain)和1954年再版的诺曼·维纳(Norman Weiner)的《人有人的用处》(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他们开创了一个映射在政治上的新的技术工程范式,试图完全绕过意识形态和叙事。这是一个以二进制计算机来调节和各控制系统及其环境与神经系统方程之间的配合的伺服系统。人类、动物和机器通过信息代码而能够相互理解。这种特殊的设计、特殊的机器似乎是20世纪50年代的范式,也是罗斯·阿什比这本书中建构与讨论的机器,它是为大脑设计的平衡装置,这种机器在一个不确定的环境中产生稳定却动态的平衡。
这种机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范式并且直接参与塑造了今天智慧城市的网络环境,以及智慧城市中的交通控制系统、物流系统、人群流动管理。这种范式也是意识形态层面的:风险的技术对冲、革命的透明性,以及资本主义世界系统运作中的生态隐喻。我希望能够找到上世纪50年代这条变幻莫测的分界线上的若干元素与当下的对应关系。
佚名 译
宫林林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