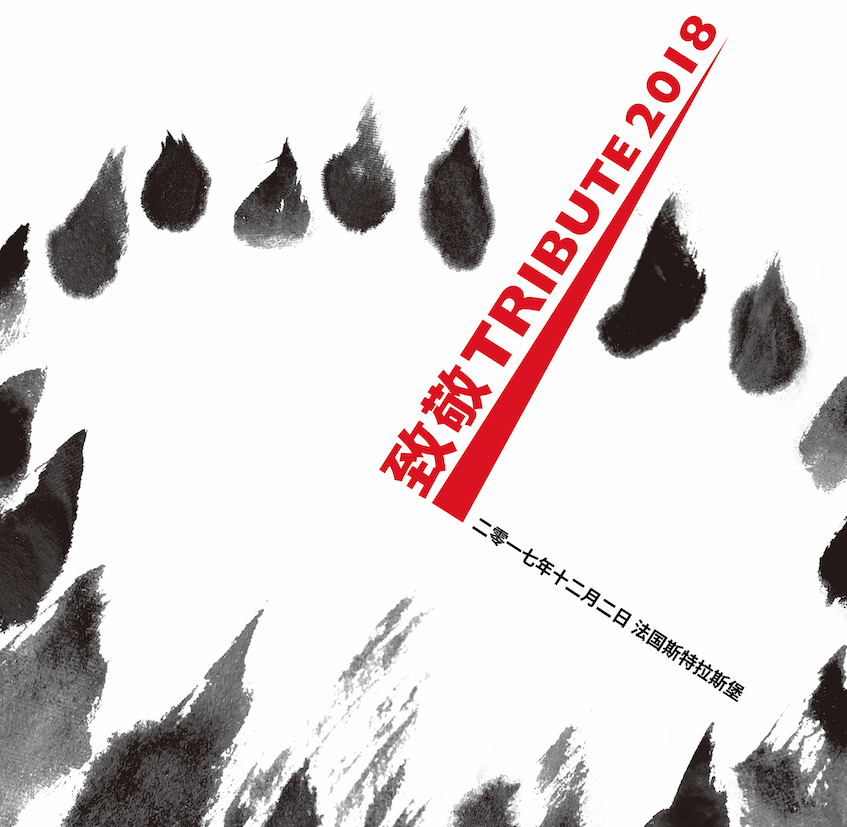2017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于2017年12月2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主办的“世纪:一个提案”论坛上的讲演
我一会儿再谈1945年——我不会完全遵守规矩——我会将不同的日期一个个连起来说,并且对过去稍作回顾。
1945年——二战的尾声,广岛事件——致使联合国代替了国际联盟而成立,也让生物学家和数学家阿尔弗雷德·洛特卡(Alfred Lotka)发表了一篇小论文,我之后还会提到这篇短文。
但我想首先讲讲1989年。这一年集合了众多事件,尽管看起来驳杂,却在事后发挥着效力,并通过它们之间出乎意料的关联,揭示出所有宣告一个新时代可能到来的事实所具有的一致性。因此,柏林墙的倒塌与日内瓦欧洲核研究理事会设立万维网在同样的日程上。
1917年,列宁向俄国的苏维埃许诺权力;2017年11月13日,《生物科学》(BioScience)上刊登了一篇共含184个国家的15364位研究人员签名的文章,希望在为时未晚时向人类发出最后的警告,一个在所谓“后真相”语境下发出的真正的“求救信号”。在1917年到2017年期间,1989年代表了一个各种层面上的转折点,这一点事后才显现出来,而且我们只有这样思考它才成立:
首先让我们从1968年至1969年开始追溯,看看“68运动”的发生——这场运动就开始于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点,随后在巴黎得到发展并以(如英美国人所说的)“大陆的”、典型法国的方式引发起反响。随后呼应它的是加州的反文化运动和伯克利大学的运动(1983年该校推出了自由协议软件),继而延伸至布拉格、东京和德国等地。不过,阿帕网(Arpanet)在1969年推行了TCP/IP标准,即我们今天所称的因特网。这些,都是对1989之前的回看。
向下追踪,就必须转向是什么导致了我们所说的平台资本主义,以及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所提出的堆栈(the stack)的形成。在“堆栈”之中,经济和技术的力量“扰乱”(我们现在用这个说法)了政治和国家权力——同时组织起了列宁当年的目标:国家的消解。与此同时,中国表现出的情况却十分不同。这使在2017年迎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背负起巨大的使命。为什么呢?
因为,在1989年到2017年之间,2000年在墨西哥,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提出将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命名为“人类纪”(Anthropocene),杰森·摩尔(Jason Moore)则称之为“资本纪”(Capitalocene)。人类纪正在重新分配所有的历史分析、所有的年代测定和所有的尺度(这对地质学家来说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问题),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科学性(scientificité)本身。
1945年,阿尔弗雷德·洛特卡(Alfred Lotka)继续推进着体外化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描述人类历史的特征,因而将在生命历史中制造分支。洛特卡在1922年,即一战后,已经发表了一篇关于熵和毁灭的奠基性文章;1945年(即广岛和奥斯维辛事件之后),在《人类生物学》(Human Biology)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作为重新开始,以科学论点扩展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启的一些视角。
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非常巧妙地利用了美国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奉行的极端自由主义政策。这场巨变无疑将使中国在短期内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会赋予这个国家一项超出历史的任务、一项极-历史的(archi-historical)或元-历史的(meta-historical)任务。
中国必须与全世界的科学共同体,以及文学届、艺术界、哲学界与法律界共同打造新的政策。中国不得不如此作为,我们也应该感激(obliger,我所说的obligr是葡萄牙语中的obrigado,意为谢谢)它如此作为。
2017年,1968年的事件即将迎来五十周年的前夕,也是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政治荒废期,整个地球已经成为了一个“意识单元”,同时也是一个失去意识、丧失判断的单元——失去意识,不仅由于网络即数字媒体的发展,也由于即将降临至这个生物圈的灾难。今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提出了这个问题,习主席也同样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中国在明日世界所占据的位置的问题。
我们的会议关心的是艺术和媒体的未来宣言——在这个有时也被称为“后媒介时代”的时代。在此应该被强调的是,如我们所知,苏格拉底时代以来的“媒介”,自从它们成为数字媒介(其中包括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便成了心智(noèse)的体外化的、药理学的器官。这些体外化的、药理学的心智器官总是会导致其对立面:即去心智化(dénoétisation)。
我们不能搞错了敌人,敌人是作为计算霸权的资本主义,计算将所有不可计算的内容抹去,而不可计算的部分是一种负熵(néguantropie),也就是在变化发展的洪流中产生分支的一切机会。
今天的媒介已参与到系统性的、全球性的去心智化过程,参与到思想的无产阶级化——马克思谈到过这种无产阶级化,在他之前,苏格拉底最先描述过无产阶级化,即知识的丧失。比如“推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是这一过程的代表。
这说明,如果长久以来被我们称为“真理”之彰显的艺术、文学和科学,能够产生经久的(即不可化约的)分支,如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财富,那么,它们必须对这些心智的体外化器官、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甚至其他许多我们尚未发现的维度进行批判。它们必须努力生产治疗的方法,重新思考这种疗法的结构和构筑术,对11月13日发出的求救信号做出回应。
艺术、文学及科学应当与中国一起承担起这项元历史或极历史的任务,而且要在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所说的“国-际”(l'Inter-nation)之中展开这个任务,这是对国际联盟和威尔逊总统在1920年发起的争论所做出的回应;也是重新思考康德在《一种以世界主义为目的的普遍历史观念》中的表述、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思想。
马塞尔·莫斯认为国-际是20世纪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中应该形成这样一种世界性(mondialité):它能够生产出独特的地方性并且尊重这些独特性,来对抗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称之为“非世界”(l’immonde)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这份“宣言”的意义。
谢谢各位的聆听。
佚名 译
宫林林 校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于2017年12月2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主办的“世纪:一个提案”论坛上的讲演
我一会儿再谈1945年——我不会完全遵守规矩——我会将不同的日期一个个连起来说,并且对过去稍作回顾。
1945年——二战的尾声,广岛事件——致使联合国代替了国际联盟而成立,也让生物学家和数学家阿尔弗雷德·洛特卡(Alfred Lotka)发表了一篇小论文,我之后还会提到这篇短文。
但我想首先讲讲1989年。这一年集合了众多事件,尽管看起来驳杂,却在事后发挥着效力,并通过它们之间出乎意料的关联,揭示出所有宣告一个新时代可能到来的事实所具有的一致性。因此,柏林墙的倒塌与日内瓦欧洲核研究理事会设立万维网在同样的日程上。
1917年,列宁向俄国的苏维埃许诺权力;2017年11月13日,《生物科学》(BioScience)上刊登了一篇共含184个国家的15364位研究人员签名的文章,希望在为时未晚时向人类发出最后的警告,一个在所谓“后真相”语境下发出的真正的“求救信号”。在1917年到2017年期间,1989年代表了一个各种层面上的转折点,这一点事后才显现出来,而且我们只有这样思考它才成立:
首先让我们从1968年至1969年开始追溯,看看“68运动”的发生——这场运动就开始于我们今天所在的这个地点,随后在巴黎得到发展并以(如英美国人所说的)“大陆的”、典型法国的方式引发起反响。随后呼应它的是加州的反文化运动和伯克利大学的运动(1983年该校推出了自由协议软件),继而延伸至布拉格、东京和德国等地。不过,阿帕网(Arpanet)在1969年推行了TCP/IP标准,即我们今天所称的因特网。这些,都是对1989之前的回看。
向下追踪,就必须转向是什么导致了我们所说的平台资本主义,以及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所提出的堆栈(the stack)的形成。在“堆栈”之中,经济和技术的力量“扰乱”(我们现在用这个说法)了政治和国家权力——同时组织起了列宁当年的目标:国家的消解。与此同时,中国表现出的情况却十分不同。这使在2017年迎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背负起巨大的使命。为什么呢?
因为,在1989年到2017年之间,2000年在墨西哥,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提出将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命名为“人类纪”(Anthropocene),杰森·摩尔(Jason Moore)则称之为“资本纪”(Capitalocene)。人类纪正在重新分配所有的历史分析、所有的年代测定和所有的尺度(这对地质学家来说是一个很有魅力的问题),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科学性(scientificité)本身。
1945年,阿尔弗雷德·洛特卡(Alfred Lotka)继续推进着体外化的概念,这个概念可以描述人类历史的特征,因而将在生命历史中制造分支。洛特卡在1922年,即一战后,已经发表了一篇关于熵和毁灭的奠基性文章;1945年(即广岛和奥斯维辛事件之后),在《人类生物学》(Human Biology)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短文作为重新开始,以科学论点扩展了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开启的一些视角。
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非常巧妙地利用了美国自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开始奉行的极端自由主义政策。这场巨变无疑将使中国在短期内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这会赋予这个国家一项超出历史的任务、一项极-历史的(archi-historical)或元-历史的(meta-historical)任务。
中国必须与全世界的科学共同体,以及文学届、艺术界、哲学界与法律界共同打造新的政策。中国不得不如此作为,我们也应该感激(obliger,我所说的obligr是葡萄牙语中的obrigado,意为谢谢)它如此作为。
2017年,1968年的事件即将迎来五十周年的前夕,也是西方主要工业国家的政治荒废期,整个地球已经成为了一个“意识单元”,同时也是一个失去意识、丧失判断的单元——失去意识,不仅由于网络即数字媒体的发展,也由于即将降临至这个生物圈的灾难。今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提出了这个问题,习主席也同样高瞻远瞩地提出了中国在明日世界所占据的位置的问题。
我们的会议关心的是艺术和媒体的未来宣言——在这个有时也被称为“后媒介时代”的时代。在此应该被强调的是,如我们所知,苏格拉底时代以来的“媒介”,自从它们成为数字媒介(其中包括人工智能和社交媒体),便成了心智(noèse)的体外化的、药理学的器官。这些体外化的、药理学的心智器官总是会导致其对立面:即去心智化(dénoétisation)。
我们不能搞错了敌人,敌人是作为计算霸权的资本主义,计算将所有不可计算的内容抹去,而不可计算的部分是一种负熵(néguantropie),也就是在变化发展的洪流中产生分支的一切机会。
今天的媒介已参与到系统性的、全球性的去心智化过程,参与到思想的无产阶级化——马克思谈到过这种无产阶级化,在他之前,苏格拉底最先描述过无产阶级化,即知识的丧失。比如“推特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就是这一过程的代表。
这说明,如果长久以来被我们称为“真理”之彰显的艺术、文学和科学,能够产生经久的(即不可化约的)分支,如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财富,那么,它们必须对这些心智的体外化器官、人工智能、社交媒体,甚至其他许多我们尚未发现的维度进行批判。它们必须努力生产治疗的方法,重新思考这种疗法的结构和构筑术,对11月13日发出的求救信号做出回应。
艺术、文学及科学应当与中国一起承担起这项元历史或极历史的任务,而且要在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所说的“国-际”(l'Inter-nation)之中展开这个任务,这是对国际联盟和威尔逊总统在1920年发起的争论所做出的回应;也是重新思考康德在《一种以世界主义为目的的普遍历史观念》中的表述、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思想。
马塞尔·莫斯认为国-际是20世纪的未来,在这个未来中应该形成这样一种世界性(mondialité):它能够生产出独特的地方性并且尊重这些独特性,来对抗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称之为“非世界”(l’immonde)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就是我们这份“宣言”的意义。
谢谢各位的聆听。
佚名 译
宫林林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