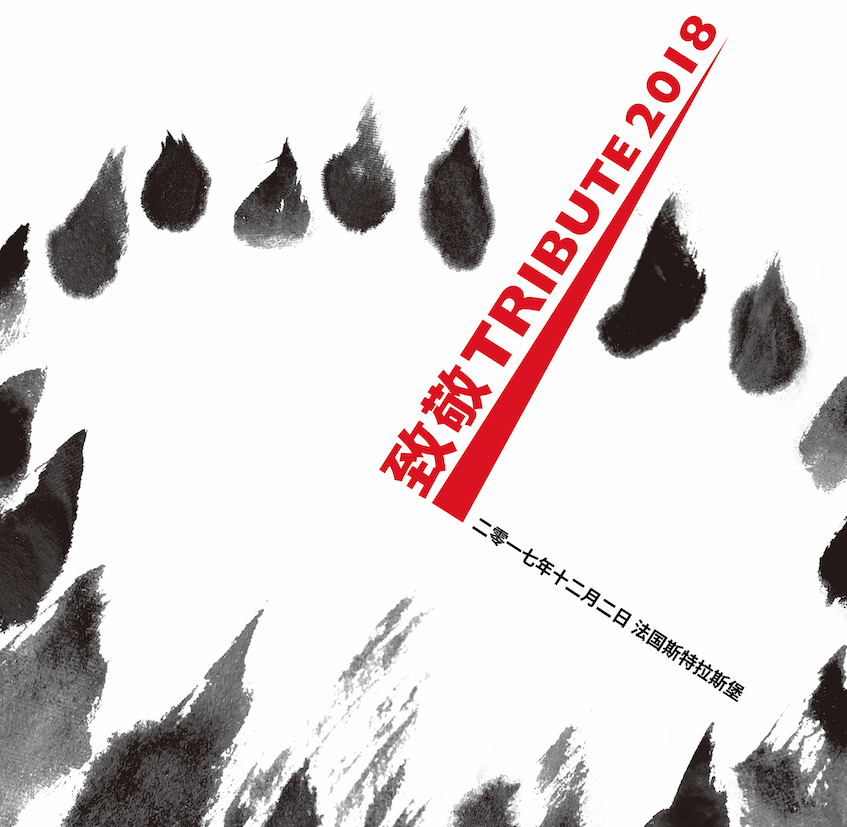2017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于2017年12月2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主办的“世纪:一个提案”论坛上的讲演
1938年伊始,视觉艺术领域产生一个强烈的隐喻:该年1月,巴黎美术画廊(Galerie des Beaux-Arts)借“国际超现实主义艺术展”(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 du Surréalisme)之际展出了萨尔瓦多·达利的装置作品《雨中计程车》(Taxi pluvieux)。作品中,车内一位长有鲨鱼头的出租车司机以及后排一位着装优雅的橱窗模特,都被艺术家安装在车内的造雨装置淋湿全身。除了雨水的折磨,达利还把活生生的蜗牛连同他搜集的饲料一并丢进车里。这一切对于车内那位被恶魔般的司机带着驶向一个没有明确方向的女性形象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折磨。然而,这一女性形象所遭受的迫害,不仅围绕这件装置本身,同时也是达利力求通过他的作品所映射出的他的超现实主义同伴们的遭遇,更重要的是引发观众对当时的全球政治浩劫的反思。艺术家通过他的超现实主义作品抨击现实中的暴行,正犹如地震仪对灾难的预警。
当时的法国正遭受政治和经济双重危机,人民阵线濒临瓦解。西班牙全面陷入血腥内战,国际纵队为捍卫新共和国艰苦战斗,而弗朗哥的大军借由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的支持,于1939年春天确立独裁统治。曾作为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革命武装杜鲁提兵团(Durruti Column)成员参与社会革命的德国艺术史家卡尔·爱因斯坦(Carl Einstein),1938年5月在深深的绝望中写下:“艺术的问题恰恰就是人类自由的问题。”而他也知道,“诗与画在机关枪面前不值一提”。苏联当时笼罩在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下,红色独裁者通过一场所谓的“莫斯科审判”肃清了党内反对派。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为对抗斯大林,创立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为目标的第四国际。在德国,社会全方面陷入独裁统治,“国家社会主义”的异见者被残酷镇压,对犹太人迫害和镇压在11月的“水晶之夜”(Novemberpogrome,又称Kristallnacht)全面爆发,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丧心病狂的驱逐和大屠杀。数不清的人背井离乡,其中包括大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延续纳粹的文化政策,自1937年开始的“堕落艺术”(Entartete Kunst)巡回展,全面批判了包括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构成主义、包豪斯、新客观主义(Neue Sachlichkeit)等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艺术成果。1938年3月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同年9月英、法、意与德国签署《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意志帝国。尽管各家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仍是一触即发。1938年的中国战场旷日持久:日本在东北盘踞七年之后,进一步加快对中国大陆的侵略,而此时中国已在国共内战中大伤元气。1937年的夏天,抗日战争爆发,而当年冬天日本攻占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大举屠杀城内超过二十万平民。尽管蒋介石不惜下令凿开黄河堤坝进行抵抗,无数村庄和城镇毁于一旦,人民死伤无数,但国民党的新大营——处于中国腹地的武汉——仍在数月的坚持后于1938年秋天被日军占领。世界范围内20世纪30年代都被打上了政治和军事冲突的烙印,所有这些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原因:反动派针对政治先锋派、民主、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潮流的激烈抵御。
即便如此,地球似乎仍旧照常运转,科学技术和商业发展预示了未来的方向。1938年,在韩国,三星品牌初创时还只是个食品公司;在瑞士,雀巢成为速溶咖啡市场的开拓者;在美国,人们发明了用尼龙鬃制成的牙刷、静电复印技术,第一部超人漫画也于这一年问世;在德国,康拉德·楚泽(Konrad Zuse)发明了第一台计算机的雏形;在瑞士,艾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fmann)首次合成出了致幻剂LSD;在法国,意大利国家足球队获得世界杯冠军——二战爆发的前夜,生活如万花筒般充斥琐碎又不那么平凡的细节。此时在看似还有政治自由的法国举办的“国际超现实主义艺术展”,恰以讽刺性颠覆的方式,将这种处境上演为一出离奇的“世界剧场”好戏。1938年,不仅是达利这件《雨中计程车》,还有杜尚(Marcel Duchamp)、沃尔夫冈·帕伦(Wolfgang Paalen)、曼·雷(Man Ray)的装置作品,以及阿尔普(Hans Arp)、恩斯特(Max Ernst)、米罗(Joan Miró)、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伊夫·唐吉(Yves Tanguy)等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共同构成超现实主义的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一个恐怖幽闭又混乱无常的荒诞情境,从心理乃至各方面,创造出一派世界动荡、风雨飘摇的不确定图景。
与此同时,这次国际超现实主义艺术展也可以看作是超现实主义这一重要艺术浪潮的绝唱。不久后这些超现实主义艺术的领军人就因艺术见解和政治理念不同而产生巨大分歧。曾与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一道组织展览的保罗·艾吕雅(Paul Eluard),出于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展览同年退出超现实主义群体;恩斯特与曼·雷紧随其后,布勒东和达利也在一年后分道扬镳。前卫艺术的阵线与全世界激进政治力量一样,都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1938年夏天,越来越痴迷精神分析理论的达利,前往伦敦拜访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并以超现实主义手法完成一幅这位精神分析大师的画像(《弗洛伊德的脑袋是一只蜗牛》)。布勒东此时变得更加政治化,他在墨西哥的旅行中见到借住在弗里达(Frida Kahlo)和里维拉(Diego Rivera)家里的托洛茨基。他们共同起草《为了独立的革命艺术宣言》(Pour un art révolutionnaire indépendant),号召艺术应该为社会革命积极准备,并支持进步艺术家们国际联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文明从未像今天这般岌岌可危。我们想到的绝不仅仅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战争。即使是‘和平’时期,艺术与科学的处境也变得完全不堪忍受。在艺术创作的领域中,想象力必须从一切羁绊中解放出来,并拒绝以任何借口加以桎梏。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于那些持有‘艺术要遵守规则哪怕违背其本性’论调的人,我们给予坚决的否定,并且反复重申我们坚定的立场——艺术要全面自由。”
然而,1930年代末几乎没有任何艺术作品能够以有效的视觉形式展现世界的构成,仅有少数几件意义深远的作品产生于这个灾难的时代。如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âncuși)在罗马尼亚特尔古日乌(Târgu Jiu)创作的,包括《无穷柱》(Colonne sans fin)在内的雕塑作品系列《纪念碑》(Denkmal ensemble),是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思考转化为抽象的表现形式;杜尚的《手提箱里的盒子》(Bôite-en-valise),有如一个便携美术馆将他个人作品纳入手提箱中,传达奔波与逃亡的主题。当然这一战火纷飞年代里,有一件艺术品堪称典范,那就是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格尔尼卡》(Guernica)。该作品创作于1937年,并于巴黎国际博览会西班牙馆展出,大约是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作品之一。毕加索将德军对这座巴斯克小镇的轰炸,以及弗朗哥妄图将罪责推卸给共和国的政治阴谋,描绘于画面中,直到今天都是对暴政与独裁的警示。如同其他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一样,毕加索并不是以贴近生活的写实方式反映政治现实,而是采用高度个人化的视角。
到1938年,德国周边的前卫艺术几乎全军覆没。自1933年纳粹取得政权,越来越严苛的文化政策导致大部分现代艺术的覆灭。尽管到1940年代还有一些温和的表现主义艺术家尝试适应新的政权,但依然无法改变局面。希特勒和他的党徒展开一场彻底的“清洗”运动:大约两万件作品被冠以“堕落艺术”之名从博物馆撤出没收,大批画家和雕塑家被学院开除,思想进步的美术馆馆长被解职,很多艺术家、经纪人、收藏家被迫流亡。1938年开始,急需外汇的“第三帝国”开始向海外市场售卖那些被罚没的“堕落”艺术品,照希特勒的说法,这些作品不过是“达达主义喧闹者、立体主义石膏匠和未来主义染织工制造的愚蠢笑话”。一开始我们可能有点疑惑,希特勒本人也曾是一个失败的不太有才华的艺术家,竟然如此激烈地诋毁前卫艺术,而我们不该忘记,类似于魏玛政权曾经对文学和音乐的排挤,视觉艺术的存在会唤起人们对自由社会的怀念,正因如此,必须将其从公众视野中铲除。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在1937年流亡于荷兰时,利用背井离乡的这段时间深刻反思了他的个人创作,并于隔年在伦敦的新伯林顿画廊(New Berlington Galleries)进行演讲。当时这里正在举办“20世纪的德国艺术”大展,以对抗德国的“堕落艺术”巡回展(Entartete Kunst)。马克斯·贝克曼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在创作中首先关心的,是隐藏于现实表象背后的理想[……]我的目标总是想抓住现实的魔力,并且将这种现实转化到绘画中,使现实中的不可见变得可见[……]这听起来也许有些相互矛盾,但这才是建构我们存在的现实。”
对于“现实魔力”的刻画,事实上并非痴迷于对现实主义的模仿式的拷贝,这种拷贝反应的也仅仅只是世界以及事物的表象而已,缺乏真实性。它应该是一种诉求,正如达利、杜尚、布朗库西、毕加索、布勒东、里维拉等人一直以来所为之不懈努力的一样。而这种诉求直至今日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即使今天政治和暴力引起的世界冲突影响着我们当下的那种矛盾以及政治性的、强制性的阐述,也存在着与1938年时性质上的不同,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一个共同点:不论内战、恐袭、分离主义运动还是民族主义孤立地看起来有多么不同,我们最终都面临着一种防御性反应,从根源上来讲这与1938年的状况无异。这个问题在今天就是涉及生活各领域的经济全球化,以及以民族和宗教之名追求国际经济霸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渴望的社会革命,在21世纪不再可行,因为资本化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取得了全面胜利。那么接下来要怎么办?艺术家能做什么?我们这些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又能帮什么忙?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将是充满冲突的世纪,也同样充满机遇,而机遇并非存在于全球化之中,近期对于全球化的批评都没有击中要害。今天,就同以前一样,我们依然召唤艺术的全面自由,这种艺术基于世界范围的交流,只有这样才能真的反映现实,即,通过“现实的魔力”让我们睁开双眼看到“自身存在的奥秘”。鉴于当下所面临的威胁,艺术已经不能退回私人领域,无法退回到纯粹审美或祥和,因为,正如卡尔·爱因斯坦所说:“艺术的问题恰恰就是人类自由的问题。”
凯文·库克(Kevin Cook) 译
李鲲 校译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美术学院于2017年12月2日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主办的“世纪:一个提案”论坛上的讲演
1938年伊始,视觉艺术领域产生一个强烈的隐喻:该年1月,巴黎美术画廊(Galerie des Beaux-Arts)借“国际超现实主义艺术展”(Exposition internationale du Surréalisme)之际展出了萨尔瓦多·达利的装置作品《雨中计程车》(Taxi pluvieux)。作品中,车内一位长有鲨鱼头的出租车司机以及后排一位着装优雅的橱窗模特,都被艺术家安装在车内的造雨装置淋湿全身。除了雨水的折磨,达利还把活生生的蜗牛连同他搜集的饲料一并丢进车里。这一切对于车内那位被恶魔般的司机带着驶向一个没有明确方向的女性形象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折磨。然而,这一女性形象所遭受的迫害,不仅围绕这件装置本身,同时也是达利力求通过他的作品所映射出的他的超现实主义同伴们的遭遇,更重要的是引发观众对当时的全球政治浩劫的反思。艺术家通过他的超现实主义作品抨击现实中的暴行,正犹如地震仪对灾难的预警。
当时的法国正遭受政治和经济双重危机,人民阵线濒临瓦解。西班牙全面陷入血腥内战,国际纵队为捍卫新共和国艰苦战斗,而弗朗哥的大军借由纳粹德国与法西斯意大利的支持,于1939年春天确立独裁统治。曾作为西班牙无政府主义革命武装杜鲁提兵团(Durruti Column)成员参与社会革命的德国艺术史家卡尔·爱因斯坦(Carl Einstein),1938年5月在深深的绝望中写下:“艺术的问题恰恰就是人类自由的问题。”而他也知道,“诗与画在机关枪面前不值一提”。苏联当时笼罩在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下,红色独裁者通过一场所谓的“莫斯科审判”肃清了党内反对派。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为对抗斯大林,创立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为目标的第四国际。在德国,社会全方面陷入独裁统治,“国家社会主义”的异见者被残酷镇压,对犹太人迫害和镇压在11月的“水晶之夜”(Novemberpogrome,又称Kristallnacht)全面爆发,随之而来的是更加丧心病狂的驱逐和大屠杀。数不清的人背井离乡,其中包括大批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延续纳粹的文化政策,自1937年开始的“堕落艺术”(Entartete Kunst)巡回展,全面批判了包括表现主义、达达主义、构成主义、包豪斯、新客观主义(Neue Sachlichkeit)等魏玛共和国时期的艺术成果。1938年3月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同年9月英、法、意与德国签署《慕尼黑协定》,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割让给德意志帝国。尽管各家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仍是一触即发。1938年的中国战场旷日持久:日本在东北盘踞七年之后,进一步加快对中国大陆的侵略,而此时中国已在国共内战中大伤元气。1937年的夏天,抗日战争爆发,而当年冬天日本攻占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南京,大举屠杀城内超过二十万平民。尽管蒋介石不惜下令凿开黄河堤坝进行抵抗,无数村庄和城镇毁于一旦,人民死伤无数,但国民党的新大营——处于中国腹地的武汉——仍在数月的坚持后于1938年秋天被日军占领。世界范围内20世纪30年代都被打上了政治和军事冲突的烙印,所有这些背后都有一个相同的原因:反动派针对政治先锋派、民主、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潮流的激烈抵御。
即便如此,地球似乎仍旧照常运转,科学技术和商业发展预示了未来的方向。1938年,在韩国,三星品牌初创时还只是个食品公司;在瑞士,雀巢成为速溶咖啡市场的开拓者;在美国,人们发明了用尼龙鬃制成的牙刷、静电复印技术,第一部超人漫画也于这一年问世;在德国,康拉德·楚泽(Konrad Zuse)发明了第一台计算机的雏形;在瑞士,艾伯特·霍夫曼(Albert Hoffmann)首次合成出了致幻剂LSD;在法国,意大利国家足球队获得世界杯冠军——二战爆发的前夜,生活如万花筒般充斥琐碎又不那么平凡的细节。此时在看似还有政治自由的法国举办的“国际超现实主义艺术展”,恰以讽刺性颠覆的方式,将这种处境上演为一出离奇的“世界剧场”好戏。1938年,不仅是达利这件《雨中计程车》,还有杜尚(Marcel Duchamp)、沃尔夫冈·帕伦(Wolfgang Paalen)、曼·雷(Man Ray)的装置作品,以及阿尔普(Hans Arp)、恩斯特(Max Ernst)、米罗(Joan Miró)、安德烈·马松(André Masson)、伊夫·唐吉(Yves Tanguy)等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共同构成超现实主义的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一个恐怖幽闭又混乱无常的荒诞情境,从心理乃至各方面,创造出一派世界动荡、风雨飘摇的不确定图景。
与此同时,这次国际超现实主义艺术展也可以看作是超现实主义这一重要艺术浪潮的绝唱。不久后这些超现实主义艺术的领军人就因艺术见解和政治理念不同而产生巨大分歧。曾与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一道组织展览的保罗·艾吕雅(Paul Eluard),出于斯大林主义的倾向,展览同年退出超现实主义群体;恩斯特与曼·雷紧随其后,布勒东和达利也在一年后分道扬镳。前卫艺术的阵线与全世界激进政治力量一样,都处于分崩离析的境地。1938年夏天,越来越痴迷精神分析理论的达利,前往伦敦拜访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并以超现实主义手法完成一幅这位精神分析大师的画像(《弗洛伊德的脑袋是一只蜗牛》)。布勒东此时变得更加政治化,他在墨西哥的旅行中见到借住在弗里达(Frida Kahlo)和里维拉(Diego Rivera)家里的托洛茨基。他们共同起草《为了独立的革命艺术宣言》(Pour un art révolutionnaire indépendant),号召艺术应该为社会革命积极准备,并支持进步艺术家们国际联合:“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文明从未像今天这般岌岌可危。我们想到的绝不仅仅是即将到来的世界战争。即使是‘和平’时期,艺术与科学的处境也变得完全不堪忍受。在艺术创作的领域中,想象力必须从一切羁绊中解放出来,并拒绝以任何借口加以桎梏。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对于那些持有‘艺术要遵守规则哪怕违背其本性’论调的人,我们给予坚决的否定,并且反复重申我们坚定的立场——艺术要全面自由。”
然而,1930年代末几乎没有任何艺术作品能够以有效的视觉形式展现世界的构成,仅有少数几件意义深远的作品产生于这个灾难的时代。如布朗库西(Constantin Brâncuși)在罗马尼亚特尔古日乌(Târgu Jiu)创作的,包括《无穷柱》(Colonne sans fin)在内的雕塑作品系列《纪念碑》(Denkmal ensemble),是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思考转化为抽象的表现形式;杜尚的《手提箱里的盒子》(Bôite-en-valise),有如一个便携美术馆将他个人作品纳入手提箱中,传达奔波与逃亡的主题。当然这一战火纷飞年代里,有一件艺术品堪称典范,那就是毕加索(Pablo Picasso)的《格尔尼卡》(Guernica)。该作品创作于1937年,并于巴黎国际博览会西班牙馆展出,大约是20世纪最重要的艺术作品之一。毕加索将德军对这座巴斯克小镇的轰炸,以及弗朗哥妄图将罪责推卸给共和国的政治阴谋,描绘于画面中,直到今天都是对暴政与独裁的警示。如同其他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一样,毕加索并不是以贴近生活的写实方式反映政治现实,而是采用高度个人化的视角。
到1938年,德国周边的前卫艺术几乎全军覆没。自1933年纳粹取得政权,越来越严苛的文化政策导致大部分现代艺术的覆灭。尽管到1940年代还有一些温和的表现主义艺术家尝试适应新的政权,但依然无法改变局面。希特勒和他的党徒展开一场彻底的“清洗”运动:大约两万件作品被冠以“堕落艺术”之名从博物馆撤出没收,大批画家和雕塑家被学院开除,思想进步的美术馆馆长被解职,很多艺术家、经纪人、收藏家被迫流亡。1938年开始,急需外汇的“第三帝国”开始向海外市场售卖那些被罚没的“堕落”艺术品,照希特勒的说法,这些作品不过是“达达主义喧闹者、立体主义石膏匠和未来主义染织工制造的愚蠢笑话”。一开始我们可能有点疑惑,希特勒本人也曾是一个失败的不太有才华的艺术家,竟然如此激烈地诋毁前卫艺术,而我们不该忘记,类似于魏玛政权曾经对文学和音乐的排挤,视觉艺术的存在会唤起人们对自由社会的怀念,正因如此,必须将其从公众视野中铲除。马克斯·贝克曼(Max Beckmann)在1937年流亡于荷兰时,利用背井离乡的这段时间深刻反思了他的个人创作,并于隔年在伦敦的新伯林顿画廊(New Berlington Galleries)进行演讲。当时这里正在举办“20世纪的德国艺术”大展,以对抗德国的“堕落艺术”巡回展(Entartete Kunst)。马克斯·贝克曼在日记里写下这样一句话:“我在创作中首先关心的,是隐藏于现实表象背后的理想[……]我的目标总是想抓住现实的魔力,并且将这种现实转化到绘画中,使现实中的不可见变得可见[……]这听起来也许有些相互矛盾,但这才是建构我们存在的现实。”
对于“现实魔力”的刻画,事实上并非痴迷于对现实主义的模仿式的拷贝,这种拷贝反应的也仅仅只是世界以及事物的表象而已,缺乏真实性。它应该是一种诉求,正如达利、杜尚、布朗库西、毕加索、布勒东、里维拉等人一直以来所为之不懈努力的一样。而这种诉求直至今日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即使今天政治和暴力引起的世界冲突影响着我们当下的那种矛盾以及政治性的、强制性的阐述,也存在着与1938年时性质上的不同,但它们之间仍然存在一个共同点:不论内战、恐袭、分离主义运动还是民族主义孤立地看起来有多么不同,我们最终都面临着一种防御性反应,从根源上来讲这与1938年的状况无异。这个问题在今天就是涉及生活各领域的经济全球化,以及以民族和宗教之名追求国际经济霸权。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许多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渴望的社会革命,在21世纪不再可行,因为资本化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取得了全面胜利。那么接下来要怎么办?艺术家能做什么?我们这些理论家和历史学家又能帮什么忙?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将是充满冲突的世纪,也同样充满机遇,而机遇并非存在于全球化之中,近期对于全球化的批评都没有击中要害。今天,就同以前一样,我们依然召唤艺术的全面自由,这种艺术基于世界范围的交流,只有这样才能真的反映现实,即,通过“现实的魔力”让我们睁开双眼看到“自身存在的奥秘”。鉴于当下所面临的威胁,艺术已经不能退回私人领域,无法退回到纯粹审美或祥和,因为,正如卡尔·爱因斯坦所说:“艺术的问题恰恰就是人类自由的问题。”
凯文·库克(Kevin Cook) 译
李鲲 校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