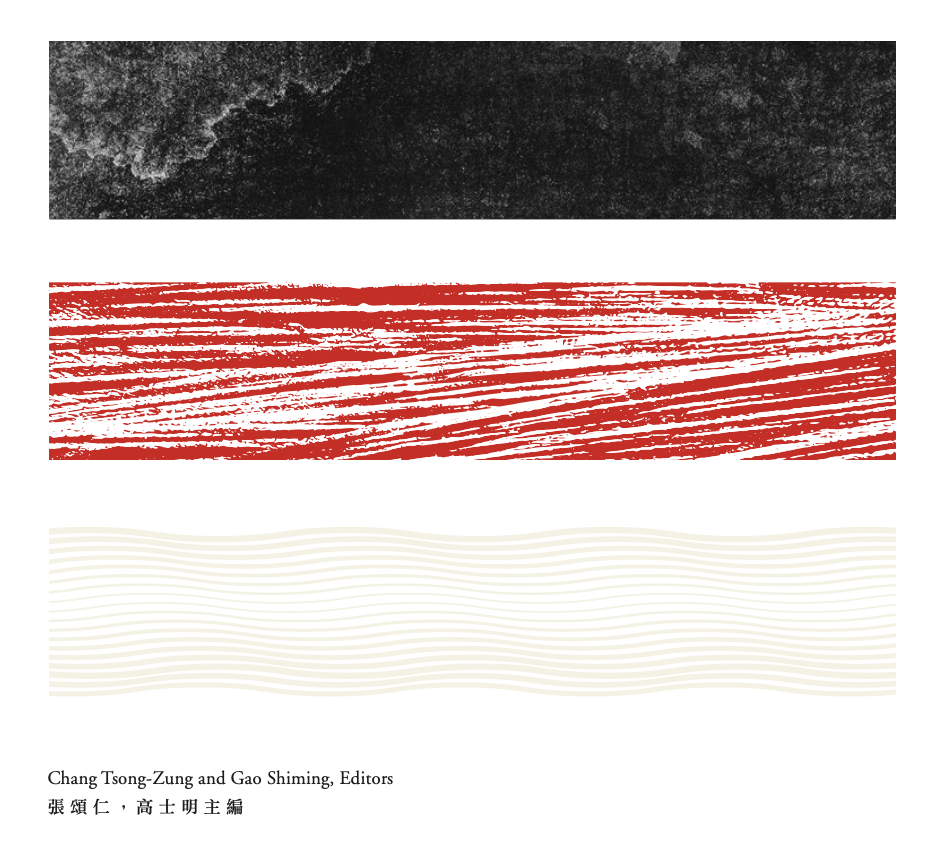2014
三十年前汉雅轩首展于1983年12月,馆址落在一座民居的大地库,我大叔启慧提供的场地。回顾三十年,既朦胧又清晰,各种机缘与际遇碰撞,才走出这个不断逛进多条歧路的艺术生涯。所以回顾三十年似乎不应该限于艺术作品的展览,而应该是一个回顾来路、重访旧梦和反省计划的时机。同时,通过一个全新而主观的角度,作为一个参与者,重新审视近代中国艺术迂回曲折的道路。这个主观的角度通过历年的合作和策展计划来展示。“汉雅一百:偏好”遴选出来的一百件“艺术物”可以说是这三十年经历的物证,也是“三个艺术世界”学术论坛的佐证。这些“物”反映了我与艺术史的遭遇,也呈现了一直保留在身边的机遇。
作为艺术史,或单纯作为我和汉雅轩的活动记录,“汉雅一百:偏好”的选择都是不全面的,无法“正确地”反映一个时代。这次作品的选择倒是刻意地回避了主流的现代论述,而游走于几种意识形态和多样历史风格的艺术生产之间。论述立场与作品选择围绕着一个我们名为“三个艺术世界”的结构。这个理论架构并列了三种艺术生产和艺术机制,包括中国传统世界、中国的社会主义世界和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尝试并置和分析这几股左右中国文化想象力的最主要力量。这个框架的立场首先拒绝了“几个中国”的说法,而替代以几个不同方式面对“现代化方案”的中国立场。中国同时介入了冷战的两方,无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体制,都全面地投入,以至同时投入了两方的陷阱,今天依然必须解决民主资本主义与社会理想主义所衍生的各种社会与文化问题。庆幸的是,文化中国尚未从中国人的记忆中完全消退,近年书画的迅速复兴是其明证。
“三个艺术世界”对历史分段不满,因为分段式的史观制造了权力等级差别。进行现代化一百年之后,我们今天清楚知道现代性承诺的美满将来和普世目标并不保证普世的美满结局。现代性的承诺引导向新的追求、新的欲望,但欲望的方向往往压抑本土的历史和在地知识,擦洗了具体的记忆与文化触觉。近二十年开始兴盛的当代艺术研究重新推敲现代社会的感性和审美追求,让我们了解现在的生活乃受制或受惠于怎么样的“文化造型”。只有深层地理解当下才可以重新给现代的艺术造型一个正确的定位,并且给被边缘化的文化感知提供一个合理的位置。三个世界的结构着眼比较和分析三种体制,其关注点是艺术物在各自的社会政治情景之下的功能。从宽阔的定义谈“体制”,是指事物所以被认定某种名分(如“艺术物”)的社会机能。于是我们问:艺术“作品”如何“工作”?艺术物与世间的日常物有什么来往?艺术物是如何在社会视线中浮现出来的?如何被定位,如何被“照顾”?
冷战两方的“现代性”历史计划各自号称对人类的未来拥有支配权,两者互不兼容。中国左右不逢源,既社且资,在冷战的左右各据一方。这两个中国世界对立了四十年才对话,至今尚处于分裂状态。讨论近代中国左右缺一不可,中国艺术史同样必须通盘考虑才算完整。
我会走上艺术的道路大概是因为成长年代对周遭世界长期的惶惑和不满。我的父母不愿意“被解放”,因此移民香港,他们对共产主义既不解且恐惧。这大概是绝大多数战后香港移民的态度。少年时我对政治的印象是毛泽东斗争运动的回响,是各种不解的话语的回声筒,像庞大发动机的噪音,随着年岁扰攘地向前滚动,背后跟随着不知名而别有企图的力量。对政治生活的直接体验,则在大跃进时代,每周末帮忙打包衣物接济在沪的亲戚。
在喇沙书院八年,我至今还很怀念耶稣会的爱尔兰神父,对受到的教育心怀感激。不过离校出国时我的状态只可形容为:被神教的历史末日吓窒。地狱的无尽黑夜,加上必须告解求恕的、细数不尽的罪行让人绝望。而且,基督教的单线历史进程与末日观,对于定期参加考试的学童绝对是一种生活的现实。后来我终于发现我成长的两种恐惧,一是对政治革命的,另一是对历史终结的,原来两者实在有深层的勾结。而且,追求未来的“现代性”狂欢也来自同一种意识形态机制的动力。对于满怀理想的少年,当年有两种选择,一是美国反主流文化的“花朵革命”,另一边是同时期的“文化大革命”。这两种看似无法兼容的选择,都从冷战核心冒出来向各自的政治机制挑战,两者都带着理想主义的反叛亢奋,可是,又互相站在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不过,两种解放运动同样引出一个疑惑:对于那些不愿意被解放,或在美国那些负担不起解放的民众,以及被解放政治所放弃的社会经济形式与历史知识又应该如何处置呢?对于“进步历史”所抛弃的遗物应该如何处置?即使其社会机制和表面形式被洗扫一新,我们知道“黑暗”的历史阶级和“封建”遗迹也不会完全消失。
回顾六七十年代,可以清楚看到这两个解放运动都没有完成他们的初衷,最后的胜利者是资本的逻辑。美国的个体自我管理精神,加上花朵革命导向新科技引领的生态运动,直接开启了美国继后的硅谷精神和新自由主义,导致新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中国于文革之后全力投入国家导引的资本主义,前因也可以追溯到毛泽东的革命。毛的革命培养了几亿名被解除了传统风俗束缚的无产阶级,结果为欲望主导的消费主义铺陈了康庄大道。被集体主义异化为个人单元的劳动者即使被剥脱了物质财产,却仍然被注满了理想的欲望。踏入一个崭新开创的世界意味着每个赤裸的个体需要重新装备起来,要配备整套全新的物质生活。花朵革命与文化革命似乎于深处被同样一股暗潮所策动。
这一百年来,开创新中国的亢奋,无论结果是建设还是祸乱,在艺术生产的角度都开展了很多矛盾和困惑的命题。台湾和香港受到美国反主流文化波及,投入了美国新潮艺术运动那种不断新旧陵替的潮流。而中国大陆社会翻天覆地的改变则来自一波连接一波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运动。从形式上看,中国大陆于社会组织的实验绝对不亚于任何极端反复的西方美术运动。这两种历史潮流,一个在于艺术试验,一个在于社会实践,各自呈现了现代前卫主义的精神。
两种营造现代性工程的方案把中国推向史无前例的社会现实。可是这种“史无前例”下面另有文章。西方早期殖民主义引进的“进步”观念和测量“进步”的尺度一直被肯定为历史进程的法则,但由于这个法则的“进步”观念受制于西方早期殖民史的观念,所以其实乃受制于现代帝国主义的权力结构。可以这样说:西方帝国主义最牢不可破、最具深远效果的成就乃是掌握历史的发言权以及对行使发言权的权力。从这角度看中国历史,最大的历史讽刺,可能是共产主义革命不自觉地为西方完成了明朝以来欧洲传教士和后来以军事做后盾的贸易商队一直追求的任务。这个任务是要把中国吸纳到西方的历史叙述中,例如时下学界争相参照希腊、罗马思想来研究中国文化历史。最终中国还是被调整到一种以西欧的想象逻辑作为主流参照的逻辑中去,而这个逻辑基本上跟自己的直觉、固有的历史文化感知是脱节的。
当今的主导艺术平台属于全球资本世界,这个平台厘定了各种艺术生产的评价和论述标准,其全球视野甚至不放过被它流放到边缘的文化生产。前期现代艺术界定了一种线性发展的想象,以“创新”的“进步性”作为线性发展的指针。长久以来,创新的标准在亚洲已被质疑,原因由于定位的权利一直保留在西方而不在本土。西方文化界提供了完整的体制结构和论述框架,伴以影响深远的资本市场,长久左右整个亚洲文化的发言权。直到二十几年前,社会主义平台还高举另一种现代的理想主义,但社会主义的文化生产似乎长期被艺术史忽略。而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又一直处于拉锯状态。现代艺术对于拒绝进入“现代”的艺术生产总是不留情面,可是在真实世界里艺术现象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不同的传承和平台之间的边界划分,其真实状态往往比较开放而且互相渗透。还待关注的悬案是那些拒绝进入新时代的艺术,其中包括某些坚持自己内部逻辑的时间表,逐步演变的传统艺术,比如书画。近年书画在拍卖市场掀起热浪,传统艺术的社会地位才令资本世界不得不另眼相看。
要表达中国的极端文化激变以及对世界想象的改造,没有什么比艺术更适合。创造一个“现代人”的主要工作,其任务之一是重新组织他的感知结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亦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近几年突然出现这么多新文化机构计划,包括公家及私家艺术馆。这些对文化机构的需求反映了这个时代感知结构的大转变,反映了我们已经到达一个阶段需要以机制来表达这些新的“感知造型”,并且以实体机构来捕捉欲望结构的改变,以及寻找对物质世界和人际关系的新形式。这应该是近年出现的新艺术馆计划大潮的社会基础。维特根斯坦很干脆地说,审美就是道德。如果这个说法合理的话,中国当代艺术界的大潮可能提供了我们当代道德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最新实验室。
现代性方案最让人伤感的是对中国历史文明的摧毁。而且,这个摧毁在我们这一代人这辈子的目击之下逐步完成。20世纪中国不同政治立场的政府,对于“进步”的理解和策略,无一不以清除历史文化的障碍作为前进的基本步骤。解放后,拆除北京城墙是一个特别强烈的视觉象征。拆除城外墙费时三年,城内墙七年,1960年完成。“文化大革命”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及近几十年全国大片清拆旧小区的破坏式建设更无须细说。重要的是,清扫传统物质文化与思想改造的计划,跟官方的意识形态方针相辅相成。中国人历史文明思维被改造之彻底,以一个具体例子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政权放弃对政治年历的主导权。解放中国但拒绝开元,所以而今人民共和第六十四年变成耶稣年历两千零十三年,2013年。中国历史主动被并合到欧洲的历史论述中。
中国百年革命的努力全以欧洲启蒙为指标,这个文明路向的转移今天表现在每个国人的身上。现代中国人无论思维的语言、对世界的欲望还是对历史和未来的想象皆焕然一新。可是中国的启蒙解放成果,更像把中国解放成为外国,成为异邦。1924年泰戈尔来访中国正好赶上五四运动的风潮,他指出了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政体的缺陷,并强烈批判正在积极国家军事化的日本。泰戈尔的立场对质了全盘西化的狭隘无知,当时备受抨击,以致这一幕重要的中印文化交流无疾而终。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启蒙已经完成任务,现在当务之急是“去启蒙”的工作,我们需要审视现代革命的光荣历史,从中发掘“西化”以外的现代意义,打开未被发挥的潜能,同时认真思考现代中国文化深度被殖民的现实。在这个历史关头,重新团结亚洲,尤其印度和东亚知识界,参考另类建设现代性的方式,如印度漫长的抗殖民经验,是极有必要的。
自道光年割让以来,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一直是远眺中国文明剧变的观景台。对香港本地人而言,殖民主的世界无异属于外国。但民国立国以来,中国的政治斗争又令这个外国殖民地成为国人躲避政治风头的绝佳避风港。前现代中国的世界,不合时宜的士大夫以各种“隐逸山林”的渠道回避政治风波。到了现代,隐逸的山林赫然被外国殖民地替代。从中国大历史看香港的地位,其历史任务似乎是给现代进程所遗弃的人事与物事作临时庇护站。晚清以降,香港的角色一直是个中介站、谈判所、议论空间、缓冲地带。作为殖民地,香港又是被殖民现代性经营出来的一个成功典范。这个现代性的逻辑又以苛刻的商业竞争和宗主国对殖民地施行的权力阶级政治为特征。所以在香港,殖民政治散发的强烈信息是:世界中心处于海外。我年轻时对终极恐惧的噩梦可能就是来自这种既极端现代但又属于遥远他处的感受。
对于现代中国,香港经验的启示是:殖民现代性与本土性顽固生命力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和磨合关系。回顾中国历史,我们发现香港的地方身份应该从反面来定义。香港身份来自意识形态未能包揽的外部、大论述的剩余物。殖民资本主义有赖剥削“现代论述”以外的世界作为扩充资源的法外之地。香港身份也属于这种另类资源的法外之地。从这个思路推敲,中国越是激进地奔前拥抱现代性,只会越激进地放弃本身的特殊资源,原因是,激进的现代性只会令中国很轻率地消耗前人历史累积起来的底气。这种底气本应是中国从资本主义现代性出走的资源,中国的历史资源才是现代性意识形态以外的天空。
话说回头,中国革命的自我肯定虽然无法绕过西方现代性充满漏洞的普世主义,可是革命先烈打破历史循环,彻底把自我打碎重新再来,这种开天辟地的大气概是举世所无的。这种气魄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的缺憾,这种气魄的秘密也是启蒙意识型态无法译码的。问题是如何磨合民族自主、传统的文明天下理想、追求现代启蒙这几股相互盘结又纠缠不清的力量。如何了解这些动力所蕴含的意义,如何承接这百年经验对后人的遗产,的确还需等待时日。“三个艺术世界”通过艺术生产角度来思考这复杂的一个世纪,发现还有其他无法清楚辨识的因素和无名的动力,因此知道全盘的历史方案永远无法毫无遗漏地整合天下。每个人心底里总有一丝无政府主义的庆幸,所以我们应该庆幸世界还有遗漏,庆幸社会的密缝间还荡漾着任何大一统都无法彻底征服的江湖。
最值得中国艺术关注的大题目,应该就是大文明的崩溃与重新自我发明的故事。今天目睹资本流窜的狂欢,国人争相走告盛世,窃自不敢或忘衣冠沦丧之痛。如何消化这种文明的剧变,是艺术界必须参与进来的工程。其中蕴藏的历史消息不仅是中国自己争气得来的启示,亦是现代世界的共同智慧。这种以整个文明的无比代价换取回来的智慧,来自对两个史无前例的历史实验的彻底投入。此中的代价虽然不足为外人道,但对于探索历史不测的轨迹,对于中国以及全球世界都有删订春秋的价值。
2014年
三十年前汉雅轩首展于1983年12月,馆址落在一座民居的大地库,我大叔启慧提供的场地。回顾三十年,既朦胧又清晰,各种机缘与际遇碰撞,才走出这个不断逛进多条歧路的艺术生涯。所以回顾三十年似乎不应该限于艺术作品的展览,而应该是一个回顾来路、重访旧梦和反省计划的时机。同时,通过一个全新而主观的角度,作为一个参与者,重新审视近代中国艺术迂回曲折的道路。这个主观的角度通过历年的合作和策展计划来展示。“汉雅一百:偏好”遴选出来的一百件“艺术物”可以说是这三十年经历的物证,也是“三个艺术世界”学术论坛的佐证。这些“物”反映了我与艺术史的遭遇,也呈现了一直保留在身边的机遇。
作为艺术史,或单纯作为我和汉雅轩的活动记录,“汉雅一百:偏好”的选择都是不全面的,无法“正确地”反映一个时代。这次作品的选择倒是刻意地回避了主流的现代论述,而游走于几种意识形态和多样历史风格的艺术生产之间。论述立场与作品选择围绕着一个我们名为“三个艺术世界”的结构。这个理论架构并列了三种艺术生产和艺术机制,包括中国传统世界、中国的社会主义世界和全球资本主义世界,尝试并置和分析这几股左右中国文化想象力的最主要力量。这个框架的立场首先拒绝了“几个中国”的说法,而替代以几个不同方式面对“现代化方案”的中国立场。中国同时介入了冷战的两方,无论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体制,都全面地投入,以至同时投入了两方的陷阱,今天依然必须解决民主资本主义与社会理想主义所衍生的各种社会与文化问题。庆幸的是,文化中国尚未从中国人的记忆中完全消退,近年书画的迅速复兴是其明证。
“三个艺术世界”对历史分段不满,因为分段式的史观制造了权力等级差别。进行现代化一百年之后,我们今天清楚知道现代性承诺的美满将来和普世目标并不保证普世的美满结局。现代性的承诺引导向新的追求、新的欲望,但欲望的方向往往压抑本土的历史和在地知识,擦洗了具体的记忆与文化触觉。近二十年开始兴盛的当代艺术研究重新推敲现代社会的感性和审美追求,让我们了解现在的生活乃受制或受惠于怎么样的“文化造型”。只有深层地理解当下才可以重新给现代的艺术造型一个正确的定位,并且给被边缘化的文化感知提供一个合理的位置。三个世界的结构着眼比较和分析三种体制,其关注点是艺术物在各自的社会政治情景之下的功能。从宽阔的定义谈“体制”,是指事物所以被认定某种名分(如“艺术物”)的社会机能。于是我们问:艺术“作品”如何“工作”?艺术物与世间的日常物有什么来往?艺术物是如何在社会视线中浮现出来的?如何被定位,如何被“照顾”?
冷战两方的“现代性”历史计划各自号称对人类的未来拥有支配权,两者互不兼容。中国左右不逢源,既社且资,在冷战的左右各据一方。这两个中国世界对立了四十年才对话,至今尚处于分裂状态。讨论近代中国左右缺一不可,中国艺术史同样必须通盘考虑才算完整。
我会走上艺术的道路大概是因为成长年代对周遭世界长期的惶惑和不满。我的父母不愿意“被解放”,因此移民香港,他们对共产主义既不解且恐惧。这大概是绝大多数战后香港移民的态度。少年时我对政治的印象是毛泽东斗争运动的回响,是各种不解的话语的回声筒,像庞大发动机的噪音,随着年岁扰攘地向前滚动,背后跟随着不知名而别有企图的力量。对政治生活的直接体验,则在大跃进时代,每周末帮忙打包衣物接济在沪的亲戚。
在喇沙书院八年,我至今还很怀念耶稣会的爱尔兰神父,对受到的教育心怀感激。不过离校出国时我的状态只可形容为:被神教的历史末日吓窒。地狱的无尽黑夜,加上必须告解求恕的、细数不尽的罪行让人绝望。而且,基督教的单线历史进程与末日观,对于定期参加考试的学童绝对是一种生活的现实。后来我终于发现我成长的两种恐惧,一是对政治革命的,另一是对历史终结的,原来两者实在有深层的勾结。而且,追求未来的“现代性”狂欢也来自同一种意识形态机制的动力。对于满怀理想的少年,当年有两种选择,一是美国反主流文化的“花朵革命”,另一边是同时期的“文化大革命”。这两种看似无法兼容的选择,都从冷战核心冒出来向各自的政治机制挑战,两者都带着理想主义的反叛亢奋,可是,又互相站在意识形态的对立面。不过,两种解放运动同样引出一个疑惑:对于那些不愿意被解放,或在美国那些负担不起解放的民众,以及被解放政治所放弃的社会经济形式与历史知识又应该如何处置呢?对于“进步历史”所抛弃的遗物应该如何处置?即使其社会机制和表面形式被洗扫一新,我们知道“黑暗”的历史阶级和“封建”遗迹也不会完全消失。
回顾六七十年代,可以清楚看到这两个解放运动都没有完成他们的初衷,最后的胜利者是资本的逻辑。美国的个体自我管理精神,加上花朵革命导向新科技引领的生态运动,直接开启了美国继后的硅谷精神和新自由主义,导致新时代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中国于文革之后全力投入国家导引的资本主义,前因也可以追溯到毛泽东的革命。毛的革命培养了几亿名被解除了传统风俗束缚的无产阶级,结果为欲望主导的消费主义铺陈了康庄大道。被集体主义异化为个人单元的劳动者即使被剥脱了物质财产,却仍然被注满了理想的欲望。踏入一个崭新开创的世界意味着每个赤裸的个体需要重新装备起来,要配备整套全新的物质生活。花朵革命与文化革命似乎于深处被同样一股暗潮所策动。
这一百年来,开创新中国的亢奋,无论结果是建设还是祸乱,在艺术生产的角度都开展了很多矛盾和困惑的命题。台湾和香港受到美国反主流文化波及,投入了美国新潮艺术运动那种不断新旧陵替的潮流。而中国大陆社会翻天覆地的改变则来自一波连接一波的政治斗争和意识形态运动。从形式上看,中国大陆于社会组织的实验绝对不亚于任何极端反复的西方美术运动。这两种历史潮流,一个在于艺术试验,一个在于社会实践,各自呈现了现代前卫主义的精神。
两种营造现代性工程的方案把中国推向史无前例的社会现实。可是这种“史无前例”下面另有文章。西方早期殖民主义引进的“进步”观念和测量“进步”的尺度一直被肯定为历史进程的法则,但由于这个法则的“进步”观念受制于西方早期殖民史的观念,所以其实乃受制于现代帝国主义的权力结构。可以这样说:西方帝国主义最牢不可破、最具深远效果的成就乃是掌握历史的发言权以及对行使发言权的权力。从这角度看中国历史,最大的历史讽刺,可能是共产主义革命不自觉地为西方完成了明朝以来欧洲传教士和后来以军事做后盾的贸易商队一直追求的任务。这个任务是要把中国吸纳到西方的历史叙述中,例如时下学界争相参照希腊、罗马思想来研究中国文化历史。最终中国还是被调整到一种以西欧的想象逻辑作为主流参照的逻辑中去,而这个逻辑基本上跟自己的直觉、固有的历史文化感知是脱节的。
当今的主导艺术平台属于全球资本世界,这个平台厘定了各种艺术生产的评价和论述标准,其全球视野甚至不放过被它流放到边缘的文化生产。前期现代艺术界定了一种线性发展的想象,以“创新”的“进步性”作为线性发展的指针。长久以来,创新的标准在亚洲已被质疑,原因由于定位的权利一直保留在西方而不在本土。西方文化界提供了完整的体制结构和论述框架,伴以影响深远的资本市场,长久左右整个亚洲文化的发言权。直到二十几年前,社会主义平台还高举另一种现代的理想主义,但社会主义的文化生产似乎长期被艺术史忽略。而传统艺术与现代艺术又一直处于拉锯状态。现代艺术对于拒绝进入“现代”的艺术生产总是不留情面,可是在真实世界里艺术现象是极其错综复杂的,不同的传承和平台之间的边界划分,其真实状态往往比较开放而且互相渗透。还待关注的悬案是那些拒绝进入新时代的艺术,其中包括某些坚持自己内部逻辑的时间表,逐步演变的传统艺术,比如书画。近年书画在拍卖市场掀起热浪,传统艺术的社会地位才令资本世界不得不另眼相看。
要表达中国的极端文化激变以及对世界想象的改造,没有什么比艺术更适合。创造一个“现代人”的主要工作,其任务之一是重新组织他的感知结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亦可以明白为什么中国近几年突然出现这么多新文化机构计划,包括公家及私家艺术馆。这些对文化机构的需求反映了这个时代感知结构的大转变,反映了我们已经到达一个阶段需要以机制来表达这些新的“感知造型”,并且以实体机构来捕捉欲望结构的改变,以及寻找对物质世界和人际关系的新形式。这应该是近年出现的新艺术馆计划大潮的社会基础。维特根斯坦很干脆地说,审美就是道德。如果这个说法合理的话,中国当代艺术界的大潮可能提供了我们当代道德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最新实验室。
现代性方案最让人伤感的是对中国历史文明的摧毁。而且,这个摧毁在我们这一代人这辈子的目击之下逐步完成。20世纪中国不同政治立场的政府,对于“进步”的理解和策略,无一不以清除历史文化的障碍作为前进的基本步骤。解放后,拆除北京城墙是一个特别强烈的视觉象征。拆除城外墙费时三年,城内墙七年,1960年完成。“文化大革命”翻天覆地的社会改造,及近几十年全国大片清拆旧小区的破坏式建设更无须细说。重要的是,清扫传统物质文化与思想改造的计划,跟官方的意识形态方针相辅相成。中国人历史文明思维被改造之彻底,以一个具体例子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政权放弃对政治年历的主导权。解放中国但拒绝开元,所以而今人民共和第六十四年变成耶稣年历两千零十三年,2013年。中国历史主动被并合到欧洲的历史论述中。
中国百年革命的努力全以欧洲启蒙为指标,这个文明路向的转移今天表现在每个国人的身上。现代中国人无论思维的语言、对世界的欲望还是对历史和未来的想象皆焕然一新。可是中国的启蒙解放成果,更像把中国解放成为外国,成为异邦。1924年泰戈尔来访中国正好赶上五四运动的风潮,他指出了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政体的缺陷,并强烈批判正在积极国家军事化的日本。泰戈尔的立场对质了全盘西化的狭隘无知,当时备受抨击,以致这一幕重要的中印文化交流无疾而终。今天,中国的现代化启蒙已经完成任务,现在当务之急是“去启蒙”的工作,我们需要审视现代革命的光荣历史,从中发掘“西化”以外的现代意义,打开未被发挥的潜能,同时认真思考现代中国文化深度被殖民的现实。在这个历史关头,重新团结亚洲,尤其印度和东亚知识界,参考另类建设现代性的方式,如印度漫长的抗殖民经验,是极有必要的。
自道光年割让以来,作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一直是远眺中国文明剧变的观景台。对香港本地人而言,殖民主的世界无异属于外国。但民国立国以来,中国的政治斗争又令这个外国殖民地成为国人躲避政治风头的绝佳避风港。前现代中国的世界,不合时宜的士大夫以各种“隐逸山林”的渠道回避政治风波。到了现代,隐逸的山林赫然被外国殖民地替代。从中国大历史看香港的地位,其历史任务似乎是给现代进程所遗弃的人事与物事作临时庇护站。晚清以降,香港的角色一直是个中介站、谈判所、议论空间、缓冲地带。作为殖民地,香港又是被殖民现代性经营出来的一个成功典范。这个现代性的逻辑又以苛刻的商业竞争和宗主国对殖民地施行的权力阶级政治为特征。所以在香港,殖民政治散发的强烈信息是:世界中心处于海外。我年轻时对终极恐惧的噩梦可能就是来自这种既极端现代但又属于遥远他处的感受。
对于现代中国,香港经验的启示是:殖民现代性与本土性顽固生命力这两者之间的张力和磨合关系。回顾中国历史,我们发现香港的地方身份应该从反面来定义。香港身份来自意识形态未能包揽的外部、大论述的剩余物。殖民资本主义有赖剥削“现代论述”以外的世界作为扩充资源的法外之地。香港身份也属于这种另类资源的法外之地。从这个思路推敲,中国越是激进地奔前拥抱现代性,只会越激进地放弃本身的特殊资源,原因是,激进的现代性只会令中国很轻率地消耗前人历史累积起来的底气。这种底气本应是中国从资本主义现代性出走的资源,中国的历史资源才是现代性意识形态以外的天空。
话说回头,中国革命的自我肯定虽然无法绕过西方现代性充满漏洞的普世主义,可是革命先烈打破历史循环,彻底把自我打碎重新再来,这种开天辟地的大气概是举世所无的。这种气魄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的缺憾,这种气魄的秘密也是启蒙意识型态无法译码的。问题是如何磨合民族自主、传统的文明天下理想、追求现代启蒙这几股相互盘结又纠缠不清的力量。如何了解这些动力所蕴含的意义,如何承接这百年经验对后人的遗产,的确还需等待时日。“三个艺术世界”通过艺术生产角度来思考这复杂的一个世纪,发现还有其他无法清楚辨识的因素和无名的动力,因此知道全盘的历史方案永远无法毫无遗漏地整合天下。每个人心底里总有一丝无政府主义的庆幸,所以我们应该庆幸世界还有遗漏,庆幸社会的密缝间还荡漾着任何大一统都无法彻底征服的江湖。
最值得中国艺术关注的大题目,应该就是大文明的崩溃与重新自我发明的故事。今天目睹资本流窜的狂欢,国人争相走告盛世,窃自不敢或忘衣冠沦丧之痛。如何消化这种文明的剧变,是艺术界必须参与进来的工程。其中蕴藏的历史消息不仅是中国自己争气得来的启示,亦是现代世界的共同智慧。这种以整个文明的无比代价换取回来的智慧,来自对两个史无前例的历史实验的彻底投入。此中的代价虽然不足为外人道,但对于探索历史不测的轨迹,对于中国以及全球世界都有删订春秋的价值。
2014年